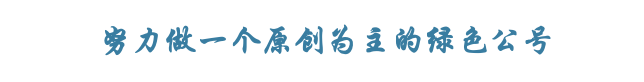来源:中国上海司法智库
发布日期:2025年09月0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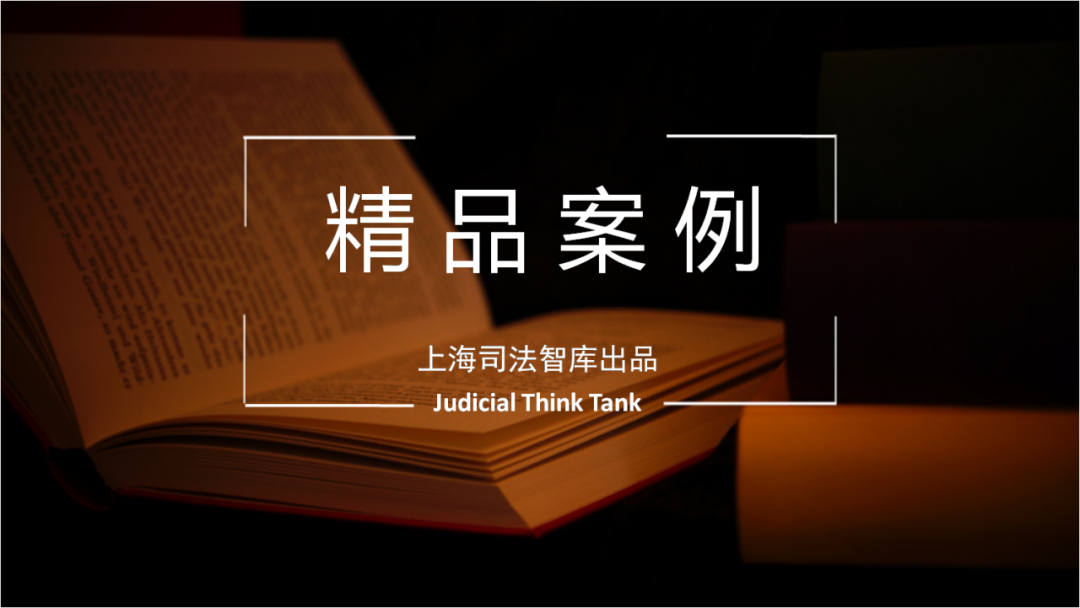
欢迎光临 精品案例 栏目
精选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公报案例、上海法院精品案例等高质量案件,深度解读、理性分析。
内容摘要
“职业骗薪”型诈骗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选择目标公司后通过虚构求职简历,隐瞒自身既没有真实工作意愿,也没有实际工作能力的真相,诱骗被害单位招聘其入职,再通过虚假打卡、编造拜访客户等方式制造努力工作的假象,骗取被害单位支付薪资的行为,且行为人以此为业。该行为模式与社会生活中,求职人员为提高入职成功率而适当包装自身履历,但入职后上班“摸鱼”或工作能力不足未给公司带来业绩而只领取底薪或被辞退的情况,在表面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因而在认定其性质时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本期案例就此类犯罪行为的性质甄别、犯罪形态、犯罪数额认定做一并梳理。
陶某诈骗案
——求职人员虚构事实进行“职业骗薪”的刑法认定
裁判要旨
1.求职人员虚构事实进行“职业骗薪”的行为究竟是劳动纠纷还是诈骗犯罪,应着重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司薪资的目的及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予以甄别。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选择目标公司并虚构求职简历欺诈入职,制造努力工作的假象,从而使得被害单位支付薪资等财物的行为,应认定诈骗罪。
2.对“着手”的判断应从行为指向性是否明确、危害性是否明显、是否已经超过犯罪预备范畴予以考察。“职业骗薪”犯罪行为,应以劳动关系建立时为“着手”。被告人在虚假入职后实际获得薪资的,即认定为既遂,对于未获得薪资的则分别根据情况认定为诈骗未遂或中止。
3.认定“职业骗薪”型诈骗数额时,需考量被害单位因诈骗行为所遭受的实质性财产损失。被害公司基于错误认识支付给骗薪行为人的底薪、社保,经劳动仲裁确认的薪资等,均应计入诈骗数额。行为人在职期间为延长诈骗时间,所支出的购买公司商品等微量资金成本,因对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无实际弥补,不应予以扣除。
基本案情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指 控 : 2020年11月至案发,被告人陶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经骗薪同伙之间相互介绍、推荐等方式选择目标单位,嗣后通过提供虚假的学历证书、工作简历、离职证明等入职材料,向被害单位虚构个人学历、金融行业从业经历,谎称手中掌握大量高净值客户,能够为被害单位完成巨额融资需求或者销售业绩,隐瞒自身既没有真实工作意愿,也没有实际工作能力的真相,先后诱使上海帝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被害单位招聘其入职。通过欺骗手段入职后,被告人陶某又通过虚假打卡签到、编造拜访客户情况、进行虚假工作汇报、雇佣他人冒充高净值客户等方式,制造自己正在为被害单位努力工作的假象,以此骗取被害单位支付的薪资,实际并未帮助被害单位产生真实业绩。经审计,目前查证被告人陶某骗得31家被害单位支付的薪资共计人民币29万余元。
2023年3月8日,被告人陶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案发后,上海市公安局冻结被告人陶某名下中国银行卡内人民币273182.30元;被告人陶某又在家属的帮助下退赔赃款人民币24000元。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陶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多次诈骗被害单位钱款,数额巨大,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陶某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被告人陶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陶某到案后有退赃行为,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庭审中,被告人陶某及其辩护人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提出陶某有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并全部退赔被害人损失,请求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指控基本相同。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9日作出(2023)沪0115刑初3813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陶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二、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后发还被害单位;扣押在案作案工具依法予以没收。判决后,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陶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多次诈骗被害单位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陶某具有坦白情节,并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并从宽处理。鉴于被告人陶某已经退出违法所得,酌情从轻处罚。
案例注解
一、“职业骗薪”型诈骗行为的认定
“职业骗薪”行为究竟系劳动纠纷还是诈骗罪,应围绕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薪资的目的,客观上是否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使得被害单位基于错误认识交付财物进行审查。
(一)行为人有无诈骗的动机和主观目的
正常入职时,行为人往往具有为入职公司提供劳动的真实目的,希冀提供满足岗位要求的劳动获取薪资,即使之后因主客观原因离职或被辞退,仍属于用工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但“职业骗薪”行为人不具有为入职公司提供劳动的真实目的,主观目的往往是通过欺诈入职、虚假工作而非法占有被害单位的钱款。
本案中,被告人陶某对被害单位的挑选并非随意、随机,而是有预谋、有针对性,系精准锁定被害单位后的求职。其锁定被害单位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一是通过骗薪同伙之间的消息互通,专门选择背景调查宽松、人事审查不严的公司,二是通过网络招聘平台,以“私募”“基金”等关键词筛选出销售需求高、坐班要求低、人事管理松的小型金融类公司。三是选择入职门槛低、工作时间自由的小型、新设的实体销售公司。之所以作如此选择系该些公司更容易入职,亦更容易同时入职多家公司以骗取基本工资。可见,行为人在入职前即不具有为该些公司提供劳务的真实目的。
(二)行为人有无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
行为人即便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没有实施欺诈行为,也不成立犯罪。因此,若未实施欺诈行为,则无必要追究其非法占有的目的。若实施了欺诈行为,则还需考虑该行为在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的过程中是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职业骗薪”案件中,具体可着重审查行为人有无在入职时伪造履历、有无提供真实劳动的行为、有无同时入职多家公司、团队协作等客观行为证据来予以审查确认。
1.有无在入职时伪造简历、从业经历
正常求职过程中,求职者往往为增加入职成功率,会对自己的简历、从业经历做一定的美化、夸大,仍属于求职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即便存在一定的提供虚假材料的情况,但如果具有提供劳动对价的真实意思和行为,则仅仅属于劳动纠纷。“职业骗薪”案件中,行为人往往为骗得招聘公司的入职机会而完全伪造简历、虚构从业经历,该行为是导致被害单位产生错误认识而将其招录的重要原因,也是行为人得以实施后续诈骗行为的关键环节。
本案中,被告人陶某为增加入职的成功率,实施了伪造简历、从业经历等虚构事实的行为。如对应招聘需求,“量身定制”入职材料,通过伪造境外学历证书、知名企业从业经历、过往薪水情况、社保缴纳记录等,将自己塑造成高度适配的应聘者。谋得面试机会后,精心准备话术,在面试中吹嘘自己手中掌握大量高净值客户,可为公司带来巨大销售业绩前景,营造自身工作能力极强的假象,致使被害单位基于错误认识而招聘其入职。事实上,被告人并不具备岗位适配能力,而是通过伪造履历等虚构事实的方式让被害单位误以为其可以胜任该岗位并与其建立劳动关系。
2.有无提供真实劳动行为
在正常的工作中,职业人员均系根据劳动合同约定向公司提供真实劳动行为,且为谋求职业发展而努力工作,即便亦存在一些员工消极怠工的情况,但仍会开展一定的岗位工作,尚未超出可容忍的正常用工程度。但“职业骗薪”行为人往往不具备工作意愿,根本无提供真实劳动的行为,而是通过向公司虚构在工作的假象,掩盖其欲非法占有的目的,从而进一步骗取公司报酬。
本案中,被告人陶某不具有为公司提供劳动的真实目的,但为让公司误以为其在努力工作,其编造拜访客户记录和工作日志等,让公司误认为其在拓展高净值客户,且该些客户具有投资意愿;对于有考勤要求的公司,还通过修改定位软件进行打卡或到公司打卡后又以跑客户为由离开公司,并通过虚假拍照打卡等方式让公司误以为其在工作;为了应付公司要求带客户的要求,更是通过雇佣退休老人冒充高净值客户等方式参加公司组织的路演、推介会等活动欺骗公司。可见,被告人通过多种方式虚构了工作假象,当然无法认定其为被害单位提供了真实劳动。
3.有无同时入职多家单位或团队协作的情况
正常情况下,提供劳动人员同一时期一般只在一家公司任职,鲜有多份工作同期入职的情况。但在“职业骗薪”的情况下,行为人为求得犯罪收益最大化,往往会同期应聘、入职多家公司。求职、入职、“工作”的过程中,还存在团伙性的特征。审查时,应着重关注行为人有无同期入职公司及数量,以及直至案发入职公司的总数,以判断其入职是否符合常情常理,并注重对该行为人以外的其他类似情况进行审查,以从多个独立犯罪事实的证据审查扩展到同类犯罪事实之间的证据印证。
本案中,在案证据显示,被告人陶某在两年四个月时间内共入职31家公司,一个月内同期在职的公司数量最高达9家,且被害单位系处于滚动变化的状态,可见该种任职情况明显不符常情常理,与一般工作调换存在本质的区别。此外,被告人陶某还供述,“职业骗薪”群体内经常会相互介绍目标公司及入职经验,因陶某面试能力强,成功率相对较高,在个别公司招聘整个销售团队入职时,其曾作为代表参加面试,伪装成销售团队团队长与公司谈判薪资。入职后,群体间还会有行为人组织进行虚假工作、统一聘请虚假客户等,因此,该种团队协作予以虚构事实的行为模式与一般的求职、入职具有明显的不同。
由此可见,尽管从个人单次入职的角度,与一般的入职后不胜任岗位被辞退的情况在形式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但从整体证据的印证情况进行审查,即可明显看出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被害单位财物的目的,与一般怠工等正常用工现象存在本质区别。因此,行为人是在非法占有被害单位薪资的主观故意下,在客观上实施了一系列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从而使得被害单位产生错误认识而建立了劳动关系,并支付薪资,从而产生损失,其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二、关于犯罪形态的认定
与一般诈骗不同,“职业骗薪”型诈骗从提交虚假资料、面试,到订立劳动合同、虚假工作,再到最后获取工资,其行为样态较多,且在欺骗行为和取得财物之间的时间间隔较长,对此,以何者作为犯罪着手的起点,涉及对被告人行为既、未遂的认定。我们认为,对于着手的判断主要应从两个角度予以考察:一是看行为的指向性是否明确和危害性是否明显,即实行行为是否已经实际接触或接近犯罪对象,是否已经对犯罪的直接客体造成了现实的、紧迫的危险。二是看行为是否已经超过“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犯罪预备范畴,是否能够直接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否已经能表现其犯罪意图。
本案中,被告人实施了多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包括锁定目标、伪造虚假入职材料和话术、与被害人建立虚假的劳动关系,虚假打卡、拜访客户、虚假汇报工作、雇佣群演欺骗公司手段制造履职假象等。但由于劳动关系的特殊性,被害单位在与行为人建立劳动关系时即具有了支付薪酬的义务,因此,行为人虽然未在入职当下立即获取薪酬,但已经对被害公司的财产法益造成现实的、紧迫的危险,应认定为已经着手实施诈骗犯罪。而在此后的过程中,被告人所实施的一系列虚构事实的行为,事实上系被告人为继续拖延在被害单位骗薪的时间以非法获取更多的薪资。基于此,对于被告人在虚假入职后,若实际获得薪资的,则认定为既遂,对于未获得薪资的则分别应根据情况认定为诈骗未遂或中止。
三、关于诈骗数额的认定
诈骗数额原则上是指行为人实际骗取的财物数额,但在实践中,行为人实际骗取所得数额与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数额往往并非完全一致。因此,认定诈骗数额时,应全面考量被害人因诈骗行为所遭受的实质性财产损失。需要注意的是,被害人财产权益所受侵犯的程度,需要将被害人财产的丧失与取得作为整体进行评价,如果没有损失,则否认犯罪的成立。同时,对于行为人为实施诈骗而支付的成本,应当重点关注该成本对被害人是否具有利用可能性,能否帮助实现预期目的,能否弥补财产损失等,判定应否从诈骗数额中扣除。“职业骗薪”案件中,所涉钱款包含了任职公司支付的工资底薪、提成、社保资金,乃至经由劳动仲裁、诉讼裁决的薪资,以及行为人在职期间付出的业绩成本等,对此应否计入诈骗数额,具体可作如下把握:
(一)被害单位支付的底薪、社保资金应计入诈骗数额
本案中,被告人与部分被害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了“底薪+提成”模式,即被告人即便没有做出业绩,也能获得底薪,包括公司仍需为行为人缴纳社保。这与上班“摸鱼”、业绩不佳的员工收入似乎有一定的相似性,对此,我们认为,行为人与被害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仅仅系其诈骗公司薪资的一个工具,不论就职前还是在职期间,行为人主观上无真实工作目的,客观上也未实际付出劳动,诈骗目标即是底薪收入,因此,其基于劳动合同所获得的底薪收入当然应计入诈骗数额。而公司为行为人支付的社保资金,虽不能为行为人实际变现取得,但缴纳在行为人名下由其获益,该金额亦是任职公司被骗用工后遭受的实际损失,与行为人诈骗手段、目的有密切关联,亦应当认定为诈骗金额。
(二)通过劳动仲裁或诉讼方式获取薪资的认定
此类“职业骗薪”案件中,发现还有行为人在任职公司发现被骗不再支付工资及时止损的情况下,以劳动仲裁、诉讼等方式讨要所谓欠薪,而仲裁委、法院在难以全面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已经或可能裁判被害单位败诉。对此,我们认为,行为人主观上以非法占有薪资为目的,客观上采取欺诈手段,致使劳动仲裁委等机关给予错误认识而运用法律强制措施将被害单位的财物交付给行为人,系三角诈骗,应以诈骗罪判处,裁判确定的薪资数额应计入诈骗数额。当然,若同时符合虚假诉讼构成要件时,属于想象竞合犯,依法从一重罪处罚。
(三)虚构业绩等诈骗成本不应从诈骗数额中扣除
本案中,被告人陶某辩称其在个别实体销售公司存在工作业绩,比如自行购买食品数百元、向朋友推销洋酒几瓶、体检卡几张等,公司为此获益,行为人被告人亦付出了资金成本。对此,我们认为,行为人向任职公司反馈的零星业绩恰恰是其虚构业绩、实践骗术的一部分,也是行为人拖延在职时间,获取任职公司信任和隐瞒犯罪事实的条件。零星业绩并非行为人出于胜任岗位要求的主观意愿,而是为了更稳妥地实现非法占有对方财产的犯罪目的。同时,公司为发展高净值客户、提高销售业绩的目的招聘行为人,行为人实际反馈的却是相差甚远的零星业绩,这显然不是公司招聘的初衷和预期目的。所谓业绩带来的利润更是远低于公司发放的工资,其对公司所遭受的财产损失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因此,虚构业绩产生的诈骗成本不应从诈骗数额中进行扣除。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案件索引
一审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3)沪0115刑初3813号
一审合议庭组成人员: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陆玮、奚燕云、周国强
编写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陆玮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夏艳
责任编辑:于涵
执行编辑:徐寅萱
⏩ 评析部分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