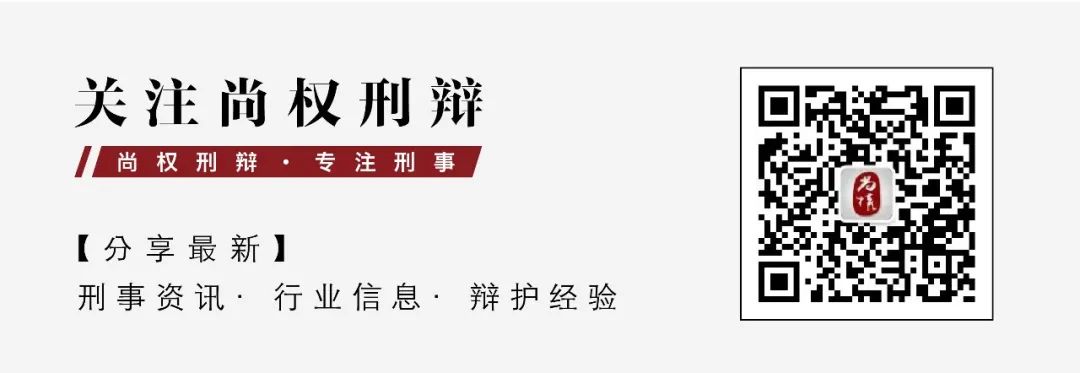来源:尚权刑辩
发布日期:2025年09月08日

摘要
传统的危险犯二分法难以合理说明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故需要引入准抽象危险犯的概念,对行为危险做出具体判断,以此来克服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二分法的不足。要认定为准抽象危险犯必须有法条指示的危险要素,故应将原先认为的部分具体危险犯作为准抽象危险犯,除此以外的抽象危险犯、情节犯、累积犯都不应包括在内。在判断标准上,应以法益为基点,将准抽象危险犯区分为针对个人法益型和针对集体法益型,进行类型化判断。对于前者,司法机关需要以社会一般人或者行为人的认识为基础,站在一般人立场判断是否存在危险。对于后者,司法机关应参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如果司法解释要求进行实质判断,司法机关对此不能予以忽略;如果司法解释只规定形式标准,司法机关原则上应做形式判断,在特殊情形下,则进行必要的限制解释。
关键词: 准抽象危险犯;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个人法益;集体法益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将危险犯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认为成立具体危险犯,法益侵害的可能需要达到现实化的程度,因而这种危险属于构成要件要素,司法机关需要结合个案情况进行具体判断,而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只是行为本身包含了侵害法益的可能性,是立法拟制的危险,只要存在行为原则上便推定危险存在。近年来,不少学者指出危险犯的二分法存在缺陷,不能合理说明我国刑法中的部分犯罪。作为解决的路径,需要扩展传统关于危险犯的分类,在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中插入一种中间形态的危险犯,独立判断与具体危险状态相分离的行为本身的危险性。
在刑法理论上,如何命名这种类型的危险犯存在一定争议。德国学者希尔施(Hirsch)区分了危险与危险性,认为危险一词只能指具体的状态,危险性则可以表示行为具有的属性,故传统理解的抽象危险犯应该表述为抽象危险性犯,而在抽象危险性犯与具体危险犯中间,存在一类具体危险性犯。施罗德(Schröder)则在保留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称谓的基础上,将具体危险性犯称为抽象—具体危险犯。在我国学界,多数学者则倾向于接受准抽象危险犯的概念。考虑到具体危险性犯、抽象—具体危险犯这些概念在理解上相对困难,准抽象危险犯的概念则与传统的抽象危险犯和具体危险犯更为协调,故本文采用准抽象危险犯的表述,将其作为第三类型的危险犯。
应当承认,准抽象危险犯概念的提出深化了危险犯的理论:一方面,其避免了抽象危险犯过于扩大处罚范围的困境,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具体危险犯所导致的处罚时间过晚的问题。因此我国晚近以来的刑事立法也逐渐倾向于采取这一立法手段,例如《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妨害安全驾驶罪与妨害药品管理罪,便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准抽象危险犯的罪名。而我国学界虽然对准抽象危险犯已经展开了一些讨论,但在本文看来,仍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准抽象危险犯概念存在的必要性问题。由于受到传统危险犯二分法的影响,目前仍有不少学者质疑准抽象危险犯概念的必要性。例如张明楷教授就认为只需要对传统抽象危险犯进行类型化解释就能解决问题,没有必要提出准抽象危险犯的概念。而赞成准抽象危险犯的学者很少对这些反对意见进行回应,只是沉溺于自身的正面说明,这显然难以被反对观点所接受,由此导致准抽象危险犯的理论基础并不稳固。
其二,准抽象危险犯的范围问题。在德国刑法中,准抽象危险犯的罪名大体上是较为明确的,学理上认可将法条规定的“足以”型犯罪或者暗含“足以”产生危险作为客观构成要件的犯罪作为准抽象危险犯。但是我国学界对此争议非常大:首先,对于是否认可我国刑法规定的“足以”型犯罪是准抽象危险犯,就存在不同意见;其次,在这一范围外究竟应认可哪些准抽象危险犯,观点也是“五花八门”。完全可以说,不同学者认定的准抽象危险犯的范围都不一致。这反过来也会成为批判准抽象危险犯的一个重要理由。
其三,准抽象危险犯的判断问题。理论上一般认为,成立准抽象危险犯不需要考虑危险状态的发生,只关心行为本身是否具备法条描述的危险特征。其判断也不用通过事后鉴定确认,而应该以理性第三人为标准进行判断。但是这只是一个抽象标准,如何将其运用于具体的准抽象危险犯罪名之中,还需要结合案例予以明确。此外,准抽象危险犯既有保护个人法益的,也有保护集体法益的,那么针对这两类不同的准抽象危险犯是否应该展开类型化的解释,传统观点也并未展开分析,对此也需要刑法理论予以回答。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将首先证成准抽象危险犯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其次,通过分析相关争议罪名,来明确准抽象危险犯的范围;最后,结合具体司法解释与案例,提出准抽象危险犯的具体判断标准。
二、讨论前提:准抽象危险犯概念存在的必要性
是否需要引入准抽象危险犯的概念,在学界存在着较大争议。只有首先明确这一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才能进一步讨论准抽象危险犯的立法范围与解释规则。因此,下文首先从我国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解释、刑法理论的角度正面证成准抽象危险犯的概念;随后对相关的批判观点予以回应,进一步明确引入准抽象危险犯概念的重要意义。
(一)准抽象危险犯概念的证成
首先,就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解释而言,确实存在一些罪名难以用传统的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进行解释。例如《刑法》第133条之二规定的妨害安全驾驶罪,法条明文规定了“危及公共安全”的要素,据此,传统观点将本罪解释为具体危险犯。但是立法者设置本罪的一个重要考虑,是为了纠正以往司法实践将大量没有产生具体危险的行为都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从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现象。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本来就是具体危险犯,如果将妨害安全驾驶罪也解释为具体危险犯,只会使得两罪难以界分,以致立法者的立法目的落空。对此,有观点认为,可以对具体危险犯的危险进行类型化解释,承认本罪中的“危及公共安全”的危险程度低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害公共安全”。但是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本罪紧邻《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的危险驾驶罪,且法定刑略高于危险驾驶罪,而危险驾驶罪是典型的抽象危险犯,只有将本罪解释为准抽象危险犯才更为合理。此外,《刑法》第114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法定最高刑为10年,这与本罪最高1年有期徒刑的刑罚相差悬殊,这种悬殊显然难以通过危险程度的差异进行解释,而必须承认两罪属于性质完全不同的危险犯。
另一方面,既然刑事立法对本罪规定了“危及公共安全”,解释者也不能完全无视这一要素的存在,如果将本罪理解为抽象危险犯,既会扩大处罚范围,也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由此,对于妨害安全驾驶罪而言,既不能用抽象危险犯解释,也不能用具体危险犯解释,只能将其作为准抽象危险犯。如果不承认这一概念,便难以合理说明立法的这一规定。
又如,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食品安全解释》)第1条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中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进行了解释,根据该规定,只要生产、销售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物质、病死、死因不明、检验检疫不合格的动物肉类等便足以构成本罪。很明显,这一司法解释并没有去判断生产、销售行为所引起的具体危险状态,而只是对行为对象进行限定性解释,这并不符合具体危险犯的定义,只能作为准抽象危险犯把握。对此,有观点认为,“判断具体案件中的危险状态,并不排除在总结司法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认定规则,根据一定情形推定具有危险状态”,从而为具体危险犯说进行辩护。本文不认同这种说法。因为具体危险犯都是结果犯,司法机关需要判断行为与危险状态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上述司法解释只是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本身进行解释,并不涉及具体的危险结果。如果严格按照这一观点进行推定,实际上是否认了本罪中因果关系存在的必要,这并不符合具体危险犯的成立要求。可见,具体危险犯中的具体危险只能由司法机关根据个案来认定,而不能由司法解释进行推定。基于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无法用具体危险犯进行理解,只能作为准抽象危险犯。
其次,从刑法理论关于危险认定的标准出发,也应该承认准抽象危险犯的概念。刑法理论一般在未遂犯与不能犯的区分中详细讨论了危险的各种判断方法,其中主要存在抽象危险说、具体危险说与客观危险说之争。抽象危险说认为要以行为人认识的事实为基础,具体危险说认为要以一般人认识的事实或者行为人的特别认知为基础,两者都以一般人的危险感作为判断基准,而客观危险说认为,要以行为当时存在的所有客观事实为基础,以科学因果法则为标准判断。因而大体可以将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判断等同于抽象危险说,将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判断等同于客观危险说。
问题在于,如果采取危险犯的二分法,具体危险说便缺失了与之相对应的犯罪类型。本文认为,在准抽象危险犯中,可以采取具体危险说的判断方法,如此一来,便能与危险判断的理论相协调。笔者曾经指出,不能在具体危险说意义上理解行为危险,这会背离其实质客观说的立场。因此对于行为危险只能在抽象危险性层面进行解释。但这是将具体危险说按通说理解为客观说的结论,倘若认为具体危险说实质上是主观理论,那么以其来判断行为危险也并无不可。周光权教授亦明确指出,具体危险说的危险指的是行为危险,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则是一种结果危险。因此针对行为危险应该根据不同的犯罪类型区分不同的判断方法:如果属于抽象危险犯,应采取抽象危险说,如果是准抽象危险犯,则应采取具体危险说。
抽象危险犯虽然原则上不允许进行危险的实质判断,但是以行为人的认知为基础,在一般人看来毫无危险的行为,也没有必要进行处罚。例如德国的放火罪属于抽象危险犯,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倘若行为人充分履行注意义务,屋内也确实无人的情况下,可以阻却放火罪的成立。又如我国的遗弃罪也是抽象危险犯,在行为人可以确实控制危险的情况下,便能否认遗弃的抽象危险。但是根据抽象危险说,只有当行为人采取了切实可信的措施,才能排除可罚性,因此出罪空间非常有限。而准抽象危险犯所依据的具体危险说,需要考虑社会一般人的认识,故不要求行为人能绝对控制危险,只要社会一般人能够认识到的事实并不危险,而在客观上也并未产生危险的,准抽象危险犯便难以成立。可见,由于采取的危险判断方法不同,准抽象危险犯较之于抽象危险犯明显扩大了出罪的范围,体现了刑法谦抑的理念。
而具体危险犯所采取的是客观危险说的判断方法,我国刑法中的放火罪属于典型的具体危险犯,因此在判断放火行为是否危害公共安全时,要将所有客观事实作为判断资料,并根据客观的因果法则判断。我国有学者批判源自日本的“独立燃烧说”,认为“独立燃烧说”是抽象危险的判断标准,适用于日本刑法中作为抽象危险犯的放火罪。这一立法例与我国存在差异,因此“独立燃烧说”在我国不具有适用可能。本文赞成这一观点,对象物处于独立燃烧的状态,并不能说明已经产生具体危险,“独立燃烧说”过于前置了处罚的时点,应当以火势蔓延这一结果危险作为放火罪成立的根据。对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言同样如此,只有当危险具有迅速蔓延性以及产生实害的高度盖然性才能成立本罪。因此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一种结果危险,按照德国学界的主流见解,只有基于纯粹偶然的原因,相应的实害才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下才能认定行为客体遭遇了具体危险。可见,具体危险犯的处罚时点较晚。而准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仍属于行为危险,只要一般人可能认识到的事实能让一般人感受到危险的,便足以成立犯罪。在这个意义上,准抽象危险犯明显前置了具体危险犯的处罚时点,体现了预防刑法观的立场。
(二)对相关批判意见的回应
如上所述,张明楷教授否认准抽象危险犯概念的存在意义,其理由大概有以下几点:其一,德国刑法中的“足以”型犯罪一般是对行为内容的描述,但是这与德国刑法中的具体危险犯并无实质不同,两者同样要求法官对个案进行判断;其二,我国刑法分则的“足以”型罪名,与德国不同,是侧重于对结果的描述,应作为具体危险犯;其三,只要细分抽象危险犯的类型,分别提出不同的解释规则,就可以替代准抽象危险犯的功能。
以上理由均存在疑问:首先,准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虽然都要求司法机关具体判断危险,但是两者的判断标准存在差异:对于准抽象危险犯,法官只能审查其行为危险性,而对于具体危险犯,则需要判断行为所引起的危险状态是否存在,只有在后者中,才有因果关系的判断必要。事实上在德国刑法中,两类犯罪的法定刑明显存在差异。例如《德国刑法典》第325条第2款规定,行为人将足以损害他人健康的有害物质排放在空气中,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这是典型的准抽象危险犯。而《德国刑法典》第330条a规定,行为人传播或排放有毒或者能产生毒性的物质,有导致他人死亡或严重损害健康危险的,处1年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这是典型的具体危险犯。可见,德国刑法对两者进行了实质的区分。
其次,马春晓博士也同样指出,德国刑法中的“足以”是作为定语修饰行为本身的危险性,而我国刑法中则是指独立的危险结果,故相关罪名只能解释为具体危险犯。但是法条的形式规定并不能影响对危险性质的实质解释,事实上德国刑法中的“足以”也并非都是作为定语修饰行为危险的,例如《德国刑法典》第311条规定,违反行政法义务,有下列行为,足以损害他人身体、生命或他人贵重财物的,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这个表述和我国刑法中的“足以”型犯罪相同,但这不妨碍德国学术界将其解释为准抽象危险犯。相反,张明楷教授列举的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虽然属于我国刑法规定的“足以”型犯罪,但是如下文所述,应将上述两罪解释为具体危险犯。不能以此作为反例说明其他“足以”型犯罪也都是具体危险犯。
最后,如何细分抽象危险犯都不能取代准抽象危险犯。张明楷教授对抽象危险犯进行类型化,旨在对部分抽象危险犯中进行危险的实质判断,即形式上虽然符合构成要件,但如果确定不存在危险,便应否认犯罪的成立。这里的实质判断主要通过反证的形式完成。但是对抽象危险犯原则上应否认实质判断。金德霍伊泽尔(Kindhäuser)指出,“一旦法益处于某种情境之中,则具体危险的全部成立条件都将齐备,而要想让法益不陷入这种情境,则只能听任偶然因素,那就可以说在此情况下存在着抽象危险。”由于立法者不愿放任客观环境中不确定的因素和行为结合以后所产生的侵害后果,故因外在环境而导致结果偶然无法发生的因素不应作为抽象危险行为的判断标准。可见,抽象危险犯的设立目的即是为了避免偶然结果的发生。如果对抽象危险犯进行实质判断,势必会背离其立法初衷。退一步而言,即便承认抽象危险犯可以反证危险,但是准抽象危险犯的危险是构成要件要素,是需要正面判断的,因此两者对危险的判断方法也不相同,不能以抽象危险犯可以实质化为由来否认准抽象危险犯的立法必要。
钱叶六教授又补充了两点理由:其一,准抽象危险犯理论与我国刑法规范不适应。因为在日本认定为准抽象危险犯的例子,都是法条没有明确描述危险要素,因而需要由法官进行具体危险的判断,因此我国刑法中的“足以”型犯罪就没有必要作为准抽象危险犯,应认定为具体危险犯;其二,准抽象危险犯的引入会模糊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的界限。
以上论述同样存在疑问。就第一点而言,日本学者论述的准抽象危险犯确实并非以法条明文规定的危险要件为基础,而是完全根据构成要件的解释来加以确定。这与德国存在较大差异。但是日本学者的认定方法存在较大问题。例如西田典之教授认为,《日本刑法典》第108条规定的向现住建筑物放火罪由于不存在公共危险的限制概念,因此属于准抽象危险犯,对于没有延烧可能的放火行为不能成立本罪。而只有那些不可能实际测量损害程度的犯罪,例如毁损名誉罪,才是典型的抽象危险犯。如此做法极大地限制了传统抽象危险犯的成立范围,并不利于保护法益。因此不能以日本刑法为例,而否认我国刑法中的准抽象危险犯。况且,即便认可日本学者的观点,实际上也只会扩大准抽象危险犯的范围,而不是去否定这一概念。
就第二点来说,如果继续采用危险犯的二分法,将准抽象危险犯并入抽象危险犯或者具体危险犯之中,确实会模糊两者的界限,因为三种危险犯的构造严格来说并不相同。但是如果采取危险犯的三分法,将准抽象危险犯从二者中独立出来,并不会影响原先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的区分,问题会成为如何界分准抽象危险犯与这两者的界限,对此,只需要合理界定好准抽象危险犯的罪名范围即可。
综上,相关质疑准抽象危险犯概念的主张难以成立,故应当充分肯定准抽象危险犯概念存在的必要性。
三、准抽象危险犯罪名范围的界定
在肯定准抽象危险犯概念的基础上,刑法理论需要清晰界定其罪名范围。下文首先对被视为准抽象危险犯标识的“足以”型犯罪进行分析,考察我国刑法中的相关罪名是否和德国一样均为准抽象危险犯;随后试图厘清准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的界限,明确某罪要认定为准抽象危险犯的具体条件;最后通过其他争议罪名性质的澄清,避免准抽象危险犯的过度扩张。
(一)“足以”型罪名的分析
与德国刑法的规定类似,在我国刑法中也有6个“足以”型危险犯,分别是: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妨害药品管理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罪。如何定性上述罪名存在争议,传统观点认为其都属于具体危险犯,部分赞成准抽象危险犯概念的学者也将其归入具体危险犯。但多数赞成准抽象危险犯概念的学者则参照德国学者的解释,认为这些属于最典型的准抽象危险犯。那么这些“足以”型犯罪究竟是属于具体危险犯还是准抽象危险犯呢?
本文认为,虽然从原则上而言,“足以使······发生危险”并不直接等于具体危险本身,而是指具体危险的前阶段,故更偏向于准抽象危险。但某一罪名是否属于准抽象危险犯,也不能只在形式上看立法是否规定“足以”,而需要综合考虑法条的体系位置以及法定刑的配置。在这个意义上,对这6个罪名便需要具体分析,其中,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不可能属于准抽象危险犯。因为其一,《刑法》第114条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等罪和第118条规定的破坏电力设备罪与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一般认为属于具体危险犯,上述犯罪的法定刑均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刑法》第116条和第117条规定的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体系上“夹在”上述罪名中间,且法定刑同样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应理解为具体危险犯;其二,《刑法》第116条和第117条都规定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这表明其行为已经产生了危险状态,即将产生实害结果,应认定为具体危险犯;其三,《刑法》第119条统一规定了第116—118条规定的四个罪名的结果加重犯,这也能说明在立法者看来,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不可能独立于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而成为准抽象危险犯。
诚然,破坏了交通工具和交通设施也不一定会形成紧迫危险,因此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的危险程度明显会弱于放火罪这一典型的具体危险犯,但这并非否认其是具体危险犯的理由。既然抽象危险犯可以划分不同的类型,那么具体危险犯也有类型化的空间。例如有学者将具体危险分为紧迫型、中间型、轻缓型三类。这就没有必要认为具体危险都必须达到紧迫的程度。域外学者甚至还提出了危险犯的四分法,例如日本学者山口厚教授在准抽象危险犯外,认为还存在准具体危险犯,其是指条文规定了危险的要素,但又没有必要达到现实紧迫程度,在紧迫危险前一阶段认定有危险即可。例如日本刑法典中交通危险罪规定的“往来之危险”。德国学者齐尚(Zieschang)在具体危险性犯外,还提出了一种具体危险状态犯,它指的是行为所引起的危险状态,但这种危险状态只是具体危险的前阶段,在德国刑法典中并没有这样的立法例。山口厚教授的准具体危险犯与齐尚的具体危险状态犯是类似的,都认为有必要扩展传统关于具体危险犯的界定。本文认为,只要承认具体危险犯的类型化,就没有必要提出准具体危险犯的概念。事实上,山口厚教授目前已经放弃了准具体危险犯的提法,而将交通危险罪作为了具体危险犯。
综上,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只是危险程度较低的具体危险犯,不是准抽象危险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上文已论证其属于准抽象危险犯,剩余的妨害药品管理罪、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和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罪也存在相应的司法解释推定这里的危险,可以被归为准抽象危险犯。
(二)准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的边界
我国刑法中除了“足以”型犯罪外,还有不少规定了“危害公共安全”“危及公共(飞行)安全”的罪名,传统观点均将上述罪名作为具体危险犯。近年来有观点指出,危及公共安全类罪名的法定刑比危害公共安全类罪名的法定刑更轻,因此前者原则上属于准抽象危险犯,例外的是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属于具体危险犯。而危害公共安全类罪名则都属于具体危险犯。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要区分“危害公共安全”和“危及公共安全”的概念。
本文认为,没有必要在语义上区分所谓的“危及”和“危害”,两者不存在什么区别,也不能简单以法定刑轻重来区分具体危险犯与准抽象危险犯。由于“抽象危险犯所禁止的未必都是低度危险的行为,法益是否发生实害,一旦逾越了行为所掌控的范围时,这时抽象危险犯所禁止的行为,普遍而言已经达到具体危险的程度”,因此抽象危险犯的法定刑不一定必然低于具体危险犯。既然如此,准抽象危险犯的法定刑也有可能较重。界定某罪是否是准抽象危险犯,主要考虑构成要件的规定。基于上述理解,三个危险物质类犯罪,即《刑法》第125条规定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第127条第1款规定的盗窃、抢夺危险物质罪、第2款规定的抢劫危险物质罪虽然规定了“危害公共安全”,且法定刑较重,但也不能理解为具体危险犯。因为与上述三罪对应的枪支、弹药、爆炸物类犯罪都是抽象危险犯。因此危险物质类犯罪中的“危害公共安全”只是用来限定解释危险物质的要素,从而使其危险性与枪支、弹药、爆炸物相平衡,应认定为准抽象危险犯。与此相对,《刑法》第124条规定的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虽然法定刑略轻,但也不宜理解为准抽象危险犯。因为本罪保护的是公众生活的平稳,而并非生命或者健康法益。根据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本罪为具体危险犯,甚至在一些情形中属于侵害犯。
在危及公共安全类犯罪中,除了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以外,其他都是准抽象危险犯,包括:《刑法》第130条规定的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第133条之一规定的运输危险化学品型危险驾驶罪,第133条之二规定的妨害安全驾驶罪。妨害安全驾驶罪的性质上文已做了详细论证。而其他两罪的性质和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不同也并非简单基于法定刑的考虑。因为对于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刑法在“危及公共安全”后,还附加了“情节严重”的限制,如果是具体危险犯则根本无需规定这一要素。而《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的前三项危险驾驶罪,都是抽象危险犯,参照前述危险物质类犯罪,第(四)项规定的“危及公共安全”明显是对危险化学品性质的限定。至于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属于具体危险犯的原因是,其构成要件中存在“尚未造成严重结果”的要素,这表明其与“造成严重后果”的实害仅一步之遥,不可能属于准抽象危险犯。当然成立本罪并不需要达到紧迫危险的程度,因此可以作为危险程度较低的具体危险犯。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具体危险犯的法定刑相对较重,但也不能认为法定刑轻的就不可能是具体危险犯。例如对于《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危险作业罪,有观点认为该罪属于抽象危险犯,也有观点将其作为准抽象危险犯,主要是考虑到本罪最高只能处1年有期徒刑。但是《刑法》第134条之一明确规定了“现实危险”的要素,现实危险只能解释为具体危险,而不能作为准抽象危险,否则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对此,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典型案例》案例5“李某远危险作业案”中明确指出,危险作业罪中“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是指客观存在的、紧迫的危险,这种危险未及时消除、持续存在,将可能随时导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因此本罪不可能是准抽象危险犯,只能是具体危险犯。至于法定刑的轻重是一个立法论的问题,只能在未来修法时予以考虑,但不能以此为由突破解释论的限制。
综上可知,要认定为准抽象危险犯必须有法条指示的危险要素,也即准抽象危险犯是从原先认为的具体危险犯中进一步划分出部分罪名从而形成的概念。要区分某一犯罪究竟属于准抽象危险犯还是具体危险犯,可以考虑如下因素:其一,法条的体系位置。同一罪名的不同行为类型之间,同一法条的不同罪名之间,相邻法条的不同罪名之间需要进行体系解释,不能出现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准抽象危险犯并存的现象。其二,法定刑的配置。虽然通过法定刑去变更罪名的“量刑反制定罪”并不合理,但是承认法定刑可以影响构成要件解释的“以刑制罪”却得到学界普遍认可。法定刑的配置有多方面的考虑,而其中行为的不法性质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规制同一行为的不同犯罪之间,如果法定刑相差悬殊,那么其性质便不可能一致。例如妨害安全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可能都属于具体危险犯。其三,构成要件的规定。如果在某罪的构成要件中出现“尚未造成严重结果”,便意味着其属于具体危险犯。反之,如果立法者在危险要素后额外附加了“情节严重”的限制,便无法再视为具体危险犯,只能是准抽象危险犯。
(三)其他争议罪名性质的澄清
除了上述所认定的准抽象危险犯外,目前在学界还有不少学者进一步扩大了准抽象危险犯的范围,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
其一,将大量传统的抽象危险犯作为准抽象危险犯。例如有学者借鉴日本学者的观点,认为只要刑法保护个人法益或者公共安全法益,并且没有规定任何危险要素的,便可以作为准抽象危险犯。据此,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与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便属于准抽象危险犯。但是如果采取这样的理解,意味着传统抽象危险犯将不复存在,这显然不利于保护法益,也不符合立法者的意图。就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而言,只能将其作为抽象危险犯。作为参照,《德国刑法典》第316条规定的醉态驾驶罪,类似于我国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对此罪的适用,德国学者认为,“有少数人援引责任原则论证个案中的一些行为不适用醉态驾驶罪,这种观点将大大削弱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举止引导效力,为一些危险的主张开启了大门。”因而对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而言,原则上应肯定规范的一般效力,除非存在适用但书的少数情况,否则不宜进行实质判断。事实上,这也是我国司法解释坚持的立场。如果将本罪作为准抽象危险犯,明显违反司法解释的规定。
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亦同样如此,因为《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假药犯罪中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实际上就是将该罪从准抽象危险犯转化为抽象危险犯,立法者的意图就是为了降低本罪的入罪门槛。根据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药品安全解释》)第19条的规定,“假药”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认定。如果仍然将该罪解释为准抽象危险犯,考虑药品对人体的危险性,实际上便完全否定了刑法与司法解释的规定,难言妥当。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准抽象危险犯不应去“侵犯”原先属于抽象危险犯的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刑法中还存在一个特殊的罪名,即《刑法》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传统观点认为本罪属于抽象危险犯,其依据是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的规定。根据该规定,有毒有害食品的认定完全取决于行政法规,这有可能会导致不存在任何危险的行为入罪。本罪虽然没有明示危险要素,但是条文中的“有毒、有害”却暗含了行为危险,这和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明显不同,因此可以认定为准抽象危险犯。2013年的解释将本罪从准抽象危险犯转变为抽象危险犯,明显存在疑问。或许正因如此,随后《食品安全解释》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第9条中规定,只有危害人体健康的,才属于这里的非食品原料。由此补充了立法暗示的危险要素。本罪也更加明显地表现出准抽象危险犯的特征。
其二,将“其他”类与“情节”类罪名作为准抽象危险犯。例如有观点认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中与“造谣、诽谤”并列的“其他方式”,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中第(一)项的“其他工具”,这些“其他”类罪名属于准抽象危险犯,刑法规定“情节严重”的罪名也属于准抽象危险犯。本文不同意上述观点,因为“情节”与“其他”均不是准抽象危险犯的特征。从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情节”有时表现为行为本身,有时表现为危险结果,有时则是实害结果,甚至有些情节还溢出了构成要件的基本不法量域,因此根本不可能根据情节的性质来确定危险犯的属性。情节应属于我国刑法的罪量要素,和危险犯的定性属于不同层面,因此不能将情节犯视为准抽象危险犯。至于“其他”的认定,司法实践只需要根据同类解释的规则处理即可,和准抽象危险犯也并无关系。
其三,将累积犯作为准抽象危险犯。有学者认为,累积犯也属于准抽象危险犯的重要类型,据此,《刑法》第338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便属于准抽象危险犯。这一观点同样存在疑问。累积犯由德国学者库伦(Kuhlen)首先提出,这一概念是为了解释《德国刑法典》第324条规定的污染水体罪,因为单次的排水行为难以达到抽象危险犯所要求的一般危险性,只有行为被大量实施才能最终侵害法益,这便是累积犯的由来。在库伦看来,累积犯和传统抽象危险犯并不相同,累积犯的危险显然更为抽象。因此如果以传统抽象危险犯为原点,累积犯和准抽象危险犯分别往两个相反的方向延伸,根本难以将两者等同。另一方面,我国刑法中的污染环境罪与德国刑法中的污染水体罪并不相同,而有其特殊性,根据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罪既有行为入罪的情形,也有结果入罪的情形。张明楷教授据此认为本罪既可能是危险犯也可能是实害犯。
综上,我国刑法规定的准抽象危险犯主要包括:《刑法》第125条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第127条盗窃、抢夺危险物质罪、抢劫危险物质罪、第130条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第133条之一运输危险化学品型危险驾驶罪、第133条之二妨害安全驾驶罪、第142条之一妨害药品管理罪、第143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第145条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第334条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罪。
四、准抽象危险犯的类型判断
以往刑法理论均未区分准抽象危险犯的具体类型,本文认为应当以法益为基点,将准抽象危险犯区分为针对个人法益型和针对集体法益型,进行类型化判断。理由在于,一个行为入罪边界的重要衡量标准在于是否存在法益侵害,而个人法益往往具有明确性,集体法益则较为抽象。因此两者需要在解释论上进行区分。虽然在准抽象危险犯中没有直接指向传统个人法益的罪名,但是有不少侵犯公共安全的犯罪。而公共安全法益由多数个人法益所组成,因此完全可以将危害公共安全的准抽象危险犯视为侵犯个人法益型,将危害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准抽象危险犯视为侵犯集体法益型。下文将分别予以阐述。
(一)侵犯个人法益型准抽象危险犯的解释
由于个人法益往往具有明确性,因此便可以采取经验层面的危险性判断,问题在于,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标准?主流观点认为,应以事后查明的行为时存在的所有事实为标准。这里的事实除了行为以外,还包括了行为时的状态、行为引起的事实状态变化等。但是,在判断结果危险时,同样也是以上述事实作为判断基础,这会导致行为危险与结果危险的区分非常模糊,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根本没有必要、也无法在事实认定方面区分所谓行为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因此,如果采取客观事实的标准,实际上会使得准抽象危险犯成为具体危险犯,准抽象危险犯的概念也就没有提出的必要了。
德国学者设例指出,如果司机无视红灯超越十字路口,就具有抽象危险,无需考虑是否有其他人出现。因为从行为人自己的事前判断来看,难以绝对排除危险。但如果这个区域由于炸弹威胁导致全员撤离,其行为就不再具有危险,因为潜在被害人从开始就被排除。我国学者对于这个结论,大致形成了两种意见:偏向于主观理论的观点认为,如果行为人没有事先确认炸弹威胁,那么其主观认知的事实中不应考虑这点,法益侵害仍有出现可能,无法排除超车行为有抽象危险。偏向于客观理论的观点主张,应当区分危险和对危险的认识,从客观事实而言,只要行为不能造成侵害结果的,就不能予以处罚,否则便是主观主义。
本文不赞成这两种观点。就主观理论而言,实际上是将准抽象危险犯当成了抽象危险犯。如果是抽象危险犯,那么这一批评便是正确的。因为抽象危险的认定完全以行为人的主观认知为基础,对于其主观上没有认识的事实不能作为危险判断的资料,所以因炸弹威胁导致人员撤离这点无关紧要。客观理论则误解了德国学者的观点,认为其在进行一个纯客观的事实判断,所以否认危险性。但危险与危险认识并不是绝对分离的两个概念,危险是主观还是客观主要取决于判断时点。在行为人实施行为的时点,并不存在客观查明的事实,有的只是一般人认识或者行为人认识的主观事实。只有在进行事后判断时,才会存在客观事实。如果以事后查明的事实来判断行为危险,则是将准抽象危险犯当成了具体危险犯。如上所述,德国学者采取的是危险认定中的具体危险说,即考虑社会一般人可能认识的事实,因此只要社会一般人能够认识到事实,即便行为人没有认知,一般人也并未感觉到危险的,便应该排除这里的准抽象危险。
本文认为,在认定准抽象危险犯时,应重点避免两方面问题:其一,将准抽象危险犯“降格”为抽象危险犯从而扩大处罚范围;其二,将准抽象危险犯“升格”为具体危险犯,从而予以不当出罪。其中前者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更为常见,例如被告人丁某因产后抑郁产生自杀念头,在工作单位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找到氰化钾的玻璃瓶,从中窃取了部分试剂,用A4纸包裹后拿回家放到卧室床头柜抽屉中。某日与丈夫吵架后,丁某倒了一杯白开水,将氰化钾倒入水中,并将剩余的氰化钾仍放入抽屉。随后其丈夫不小心误喝导致死亡。原审及二审法院均认为其行为构成盗窃危险物质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
如上所述,盗窃危险物质罪属于准抽象危险犯,不是抽象危险犯,司法机关需要具体判断行为是否“危害公共安全”。如果按照社会一般人或者行为人的认知,社会一般人并未感知到危险的,便不构成本罪。在本案中,行为人是基于自杀意图才盗取氰化钾,在其盗取后,便一直封闭在自己家中的卧室抽屉中,并未将其置于公共场所。考虑行为人的这一计划,一般人并不会感觉到其盗窃行为会危害公共安全,不应构成盗窃危险物质罪。至于其过失导致丈夫死亡的结果,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处罚便已足够。
此外,《刑法》第133条之二对妨害安全驾驶罪规定了“危及公共安全”,因此司法机关在认定“使用暴力”后,必须审查这一暴力行为有没有达到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程度,从而来确定是否符合法条规定的“危及公共安全”。但是司法实践有一些判例可能存在疑问。例如2020年被告人罗某昌与驾驶员因为停车问题发生纠纷,便翻过安全防护门,用手中购物袋击打司机,后司机停车报警。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这一行为虽然符合“使用暴力”,但是能否评价为“危及公共安全”还有疑问。从本案的视频监控来看,使用购物袋这种轻微击打对司机正常行驶的影响极为有限,司机主要系自己主动停车,而并非紧急刹车。况且车上还有安全防护门,行为人并不能完全翻越进入,因此其只击打了一次,没有实施连续击打。本文认为,这一击打行为并没有让社会一般人明显感觉到危险,没有达到准抽象危险的程度,不能认定为妨害安全驾驶罪。如果司法机关仅以“使用暴力”来入罪,便是完全忽视了“危及公共安全”的限定,从而将本罪作为抽象危险犯看待。
当然也应防止将准抽象危险犯作为具体危险犯。例如2021年行为人王某与司机任某因下车地点出现分歧,在车辆行驶中,王某用手中拐棍朝司机打去,司机见状不顾乘客安危,脱离方向盘与其争夺拐棍,后将车停在一边,继续厮打。法院认定二人行为均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这一结论应当是正确的,但是遗憾的是,法院在判决书中并没有进行说理,从而在学界引起了争议。有观点指出,驾驶者的异常举动足以阻断乘客暴力行为的因果性,因此对于乘客应认定为妨害安全驾驶罪的未遂犯。但实践一般对本罪的未遂犯并不处罚。本文认为,如果将行为引起的司机异常举动都纳入事实判断的范围,明显是以事后查明的所有事实作为判断基础,从而将本罪作为具体危险犯,并不合适。站在具体危险说的立场,司机的异常举动,无论是社会一般人还是行为人都难以认识,因此不能予以考虑。本案中用拐棍打的行为危险性明显高于用购物袋击打,基于事前判断的视角,足以将乘客的行为认定为妨害安全驾驶罪。
如果行为确已产生具体危险的,也不能仅评价为准抽象危险犯,而应该认定为相应的具体危险犯。例如2018年被告人梁某华在公交车行驶过程中,强行向左拉拽方向盘,致使行驶中的公交车失控,撞击一辆电力工程车,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法院认定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本案虽然发生于《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之前,但即便是现在发生,也应当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为公交车失控已经属于产生了具体危险的结果,满足了具体危险犯的成立要求,不能再定作为准抽象危险犯的妨害安全驾驶罪。而在车辆尚未完全失控时,需要考虑具体情况,如果车速快、人群密度大,则公共安全已面临现实的危险,行为人仍应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同时,司法机关也应慎重认定具体危险犯,避免将具体危险犯作为准抽象危险犯,从而不当扩大处罚范围。例如2013年丁某华两次用缝包针将付某的轿车刹车油管扎破,但均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这一判决存在疑问。既然破坏交通工具罪属于具体危险犯,那么便应该将行为时存在的所有客观事实均纳入考虑,包括行为引起的事实状态变化。而扎破刹车油管的行为并未对车辆有任何影响,缺乏科学因果法则的危险,难以满足具体危险犯的成立要求。要认定本案中的行为人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只能将该罪作为准抽象危险犯进行事前危险判断。但如上所述,本罪并不是准抽象危险犯,而是具体危险犯。
我国有学者认为,只有将具体危险的表征“结果化”,才能认定具体危险犯的成立。一般而言,如果行为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结果,可以作为具体危险产生的重要标志。例如2023年郭某某将王某某的面包车左前轮刹车油管割破,造成车辆制动液泄漏,导致车辆行车制动失效。法院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由于本案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结果,故成立具体危险犯并无问题。但是具体危险犯并非实害犯,并不以造成损害结果为必要。如果确已形成现实危险,在不介入偶然因素的情况下,损害结果便无法避免,也应当承认具体危险的存在。只是司法机关对此的判断需要更为严格,避免混淆具体危险犯与准抽象危险犯的成立条件。
(二)侵犯集体法益型准抽象危险犯的解释
侵犯集体法益型准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有一定特殊性。一方面,相关犯罪明显属于侵犯秩序法益的犯罪。但另一方面,既然立法规定了针对人身健康的危险要素,因此也需要承认上述犯罪同时也保护了个人法益。以妨害药品管理罪为例,虽然陈兴良教授认为,“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仅属于罪量要素,不决定保护法益的性质,因而妨害药品管理罪保护的只是药品管理秩序。但是这一要素明显提升了本罪的不法,因此属于构成要件要素,对法益的解释是存在影响的,这和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这一典型的抽象危险犯存在差异。可见,侵犯集体法益型准抽象危险犯实际上都是保护秩序法益和人身法益双重法益的犯罪,在解释论上应当考虑这一构造上的特殊性。
本文认为,这类侵害双重法益的犯罪较为复杂,两种法益既相互独立,但又相互影响。在解释秩序法益时,需要考虑这类秩序法益的根本目的仍在于保护公众健康。而在解释人身法益时,也应承认秩序法益的制约功能,不能完全采取公共安全类犯罪的出罪路径。如杜宇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在确定行为违反秩序法益后,轻易以对公众健康不存在实质损害为由排除犯罪成立,会导致“工具理性被完全消弭在目的理性的关照之中”。由此,秩序法益的地位可能会被彻底架空。在这个意义上,人身法益与秩序法益之间也并不存在主次关系。
正是因为考虑到上述犯罪危险判断的困难,相关司法解释对足以产生危险的具体情形都进行了明确规定,因此原则上涉案事实只要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便能予以认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可以机械地适用司法解释的规定,因为许多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仍然采取了形式标准,符合形式标准的不一定会具有实质危险。如果只进行形式判断,准抽象危险犯便都成为了抽象危险犯,因此仍然需要处理好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之间的关系。
从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大体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司法解释要求司法机关对危险进行具体判断。例如《药品安全解释》第7条第1款第1项规定,生产、销售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禁止使用的药品,综合生产、销售的时间、数量、禁止使用原因等情节,认为具有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现实危险。《食品安全解释》第9条规定,认定“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需要判断“危害人体健康”。第二类,司法解释只做了形式规定。例如《药品安全解释》第7条第1款第4项规定,涉案药品没有国家药品标准,且无核准的药品质量标准,但检出化学药成分的。《食品安全解释》第1条第3项规定,属于国家为防控疾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
对于第一类解释,司法机关必须进行危险的具体判断。可是目前的司法实践仍倾向于形式化处理。例如程某某通过阿里巴巴平台销售西布曲明,而西布曲明属于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禁止使用的药品,法院认为其行为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而没有具体判断销售西布曲明是否具有危害人体健康的危险。又如邓某、符某为了节约成本,将顾客吃剩的火锅汤料回收后过滤到水桶内,再放在锅里熬制,将回收的废弃油提供给顾客。法院认为,“口水油”属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列入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属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却忽视了是否“危害人体健康”的审查。上述法院判决违反了司法解释的规定,明显存在疑问。司法机关不能直接以药品或食品在行政机关的目录内就得出有罪结论,应当结合问题药品和食品的数量、危害性大小、销售人数等因素,通过相关鉴定来具体确定行为的危险,否则会混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从而过于扩大了刑事处罚的范围。
存在争议的是第二类解释,例如被告人于某销售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祖传治骨丸”,后被检测出地塞米松和吡罗昔康两种化学药成分,法院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直接认定为行为“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有观点对法院的做法提出了批判,认为是否检测出化学药和“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没有必然关联,司法机关应具体判断化学药的含量和性质。本文不赞成这一观点,而认同法院的做法。司法解释区分销售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禁止使用的药品与销售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药品具有合理性,因为前者行为的危害程度弱于后者行为,因此对于前者才要求司法机关具体判断危险来平衡这里的不法差异。倘若解释者主张对后者也要进行危险的实质判断,便完全忽视了两者的不同。此外,如上文所述,在妨害药品管理罪中,秩序法益对人身法益有制约功能,不能无止境地要求对危险进行实质判断,应当允许司法解释根据具体情况来推定危险。
当然司法解释确定的形式标准也并非毫无限制:首先,要符合刑法的相关规定。例如有法院指出,不能将从动物疫病流行国家地区输入的动物及产品直接与前述《食品安全解释》第1条第3项的规定等同,而是需要结合动物疫病是否属于食源性疾病进行判断,如果产品涉及非洲猪瘟等不会传染人的疾病或非食源性疾病,不能以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定罪处罚。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本罪的构成要件明确要求“足以造成······严重食源性疾病”。如果相关行为不能造成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当然不能构成犯罪。其次,如果没有任何法益侵害关联的,应予以出罪。比如《食品安全解释》第5条规定,超限量或者超范围滥用食品添加剂,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有判决指出,恩诺沙星是动物专属用药,在食用植物种植过程中,使用这一药物的行为,不能解释为该条中的“超范围”滥用行为。因为这一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对于食用植物没有任何影响,不应构成犯罪。最后,如果法益侵害关联较为微弱的,应当尽可能采取限制解释。例如,行为人没有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向癌症患者及家属销售乐伐替尼、曲美替尼等多种抗癌原料药。法院根据《药品安全解释》第7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以使用对象是危重病人为由,认为其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这一判决存在疑问。因为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由药品的性质决定,如果抗癌药本身有效,只是鉴于使用对象特殊需要处罚的话,法益侵害关联较弱,故需要严格限定。本文认为,司法解释规定的“危重病人”应指眼下即有生命危险的人,普通癌症患者并不属于这里的“危重病人”,本案应宣告无罪。
结 语
准抽象危险犯不仅有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为背书,而且在理论上也能整合危险判断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应承认它是一种独立的危险犯类型,与传统的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并列。关于准抽象危险犯的罪名范围在理论上存在很大争议,对此应进行具体分析:首先,“足以”型罪名并不都是准抽象危险犯,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其次,“危害公共安全”也不一定都是具体危险犯,其中的危险物质类罪属于准抽象危险犯;最后,“危及公共安全”也不一定都是准抽象危险犯,其中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属于具体危险犯。而针对个人法益的抽象危险犯、情节犯、累积犯等都不属于准抽象危险犯。
在判断方法上,准抽象危险犯应区分为针对个人法益型与集体法益型进行类型化判断。对于侵害个人法益的准抽象危险犯而言,由于个人法益具有明确性,因此可以采取经验层面的危险性判断。对此,不应当以事后查明的事实为基础,因为这会混淆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的界限。可以借鉴危险理论中的具体危险说,以社会一般人或者行为人的认识为基础,站在一般人立场判断是否存在危险。对于侵犯集体法益的抽象危险犯而言,在解释论上应考虑其同时保护秩序法益和人身法益。由于司法解释对这类准抽象危险犯都做了明文规定,因此可以参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但需要将司法解释分为要求进行实质判断和仅作形式规定两类,针对前者,司法机关必须进行危险的具体判断;针对后者,司法机关原则上采取形式判断,而在一些特殊情形下,例如法益侵害关联不存在或者较为微弱时,做出必要的限制解释。
来源:《政法论坛》2025年第5期
作者:王俊,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苏州大学公法研究中心教授
THE END
更多内容欢迎关注
尚权刑辩
尚权 · 北京总所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B座1703室
电话:010-58256011
值班 : 13011012097
邮编:100029
尚权 · 深圳分所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卓越城二期A座2104-2105
电话:0755-83181358
值班: 18118782488
邮编:518049
尚权 · 厦门分所
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1034号中外运大厦B栋1102室
电话: 0592-2080160
值班:18150908108
邮编:361010
尚权 · 合肥分所
地址:合肥市政务区潜山路188号蔚蓝商务港F座2006室
电话:0551-68998220
值班: 17318530757
邮编:230000
尚权 · 西宁分所
地址: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66号五矿云金贸中心B座12层
电话:0971-6115557
邮编:81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