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京都刑辩研究中心
发布日期:2025年09月0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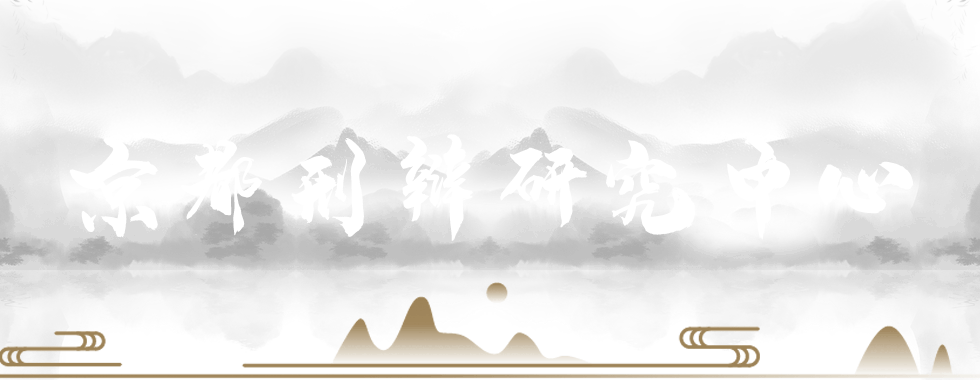

梁雅丽

傅庆涛
单位走私犯罪的认定关键系是否为单位谋取利益
某一行为属于个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通常应考虑以下因素:
•
(1)是否出于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
(2)是否由单位的决策机构依照决策程序作出决定;
(3)是否以单位名义开展业务;
(4)业务是否属于单位业务范围或与之相关;
(5)违法所得是否归属于单位。就走私犯罪而言,由于公司股权结构、经营管理、财务收支等方面的复杂性,有些认定因素或有矛盾,认定单位犯罪的关键在于走私收益是否实质上归属于单位。
一、案情简介
陈某系XE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营业范围包括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酒类等。自2018年5月7日起,陈某与叶某共享红酒购买渠道。2018年10月左右,叶某获悉境外人员“ALLY”可通过跨境电商模式以较低税率报关入境红酒,且价格便宜,遂委托“ALLY”将其在境外购买的红酒通过该模式报关入境。之后,叶某将该渠道及报价通过XE商贸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薛某告知陈某,陈某对比报价后,安排薛某联系并委托叶某将其在境外购买的红酒通过该渠道报关入境。
陈某、叶某在明知所购红酒应当以一般贸易进口方式进口的情况下,仍联系并委托“ALLY”将二人在境外购买的红酒以跨境电商模式报关入境。“ALLY”将红酒从荷兰空运至成都后,交由MD公司伪报贸易性质,通过跨境电商模式拆单报关运输进境,经机场海关计核,陈某偷逃税款人民币328436.6元,被告人叶某偷逃税款人民币170189.94元。
2019年6月19日,陈某、叶某经机场海关缉私分局电话通知到案。二人到案后,分别将33万元、18万元存入银行账户并由机场海关缉私分局冻结。
二、案件处理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叶某违反海关法规,通过他人将本应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红酒以跨境电商模式拆单进口,分别偷逃国家税款328436.6元、170189.94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案发后陈某、叶某自首,认罪态度良好,积极补缴税款,有悔罪表现,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依法可以宣告缓刑。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陈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三万元;二、被告人叶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
一审宣判后,陈某不服并提出上诉,理由包括:1、涉案红酒主要用于其个人消费及帮朋友带货,其不清楚叶某等人如何走私进口红酒;2、涉案1398瓶红酒分属XE商贸有限公司、叶某、秦某、潘某,系分别实施走私,一审未扣除秦某、潘某部分数额;3、海关计核以发票数量为准,公司实际走私230瓶,且陈某自用红酒应扣除合理减税金额2.6万元;4、本案系XE商贸有限公司犯罪;5、提货、运输及通关都由叶某联系操作,一审判决陈某刑期高于叶某,量刑不当。
三、案例解读
本案中,陈某长期从事进口红酒购销业务,熟悉进口方式及税率,明知其所购买的红酒应当以一般贸易进口方式进口。为降低成本,其明知叶某提供的“红酒国际物流报价表”中的红酒进口税金、清关费报价明显低于正常应缴税额,仍为偷逃税款安排薛某与叶某联系,委托叶某将其在境外购买的红酒通过跨境电商模式报关入境。后叶某联系并委托“ALLY”将陈某、叶某在境外购买的红酒通过跨境电商模式报关入境。叶某随后联系“ALLY”将红酒以同一方式报关入境,后交由MD公司伪报贸易性质、拆单报关运输进境,偷逃税款达到立案追诉标准,陈某、叶某行为符合走私普通货物罪的构成要件。根据案情和陈某所提理由,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二:一是是否属于单位犯罪,二是犯罪金额是否认定正确。
(一)本案是否系单位犯罪
单位犯罪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法定单位,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由有关负责人员代表单位决定,为本单位谋取利益而故意实施的,或不履行单位法律义务、过失实施的危害社会,而由法律规定为应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单位犯罪具有法定性,即刑法明确规定单位可以成立某种犯罪的,方可对单位定罪处罚。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处罚以双罚制(即对单位和单位直接责任人员均处以刑罚)为主,以单罚制(即只处罚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为辅。
认定单位犯罪的关键在于,行为实质上是否系为单位谋取利益,该利益可以是直接经济收益、潜在市场机会,或基于经营所需让渡给公司长期合作客户的应得利益。区分个人行为与单位行为,一般要考查以下因素:(1)是否出于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2)是否由单位的决策机构按程序作出决定;(3)是否以单位名义实施;(4)行为是否在单位成员的职务活动范围内,或者与单位业务相关;(5)违法所得是否归属于单位。
1、本案陈某系以公司名义开展业务。陈某系XE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有权以公司名义开展业务。陈某供述称,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红酒贸易,另两名股东基本不参与公司经营,故二人不知情走私事宜实属正常,但不能因此就否定陈某可能系为单位谋取利益。(1)本案购、销合同均是以公司名义签订,进口红酒使用的是公司配额。红酒入境收仓后,亦以公司名义与叶某、秦某、潘某签订销售合同。(2)进口红酒由公司采购部经理薛某办理,属公司日常业务,陈某作为执行董事有权安排员工处理,应首先推定为公司事务。(3)公司酒庄列有涉案红酒清单。薛某及酒庄负责人证实红酒发货至公司酒庄,清点后出货,故酒庄应有相关清单。陈某称出事后公司员工将这批酒从库存管理软件中删除,为查明真相,应依法恢复相关电子数据。
2、本案货款来源于陈某个人账户。本案之所以认定为陈某个人走私,主要是因为货款来源于陈某在境外开设的个人账户。我们认为,谁出资、谁收益是犯罪主体认定的主要依据,谁是出资人、收益人不能看表面,而应当看实质。一方面,所谓陈某出资是否只是过手,而实际上系为公司出资?另一方面,本案是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并由公司工作人员经办,在案主要证据存在矛盾。在现代公司治理模式下,公司执行董事在经营范围内干私活较为异常,在无更多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不宜仅凭红酒款从个人账户支付,即认定为陈某个人出资、受益。
3、本案销售收益去向系认定关键。关于本案是否属于单位犯罪,二审法院认为:陈某虽系XE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但走私涉案红酒未经公司账目和正常渠道,且其他股东亦不知情陈某走私红酒事宜,故不属于单位犯罪。但实践中,许多公司为规避违法犯罪调查,即便资金实质来源于公司,亦经多重周转难以溯源,这在股东少、控制紧的小公司中常见。至于股东时候回避,推脱对违法犯罪不知情,实属人性之常。因此,笔者对二审理由不敢苟同。如前所述,行为实质上系为单位谋取利益才是认定单位犯罪的关键。本案中陈某以单位名义签订合同,款项从个人账户支付,应重点调查案件矛盾之处,查清货款最终是否来源于公司,陈某是否假借公司名义谋取私利,尤其应查清红酒销售款的去向。如果红酒销售收益最终归于公司,则应依法认定为单位犯罪。
(二)关于本案的犯罪金额
本案陈某还提出涉案红酒主要用于其个人消费,自用部分应扣除合理减税金额2.6万元,以及秦某、潘某消费的红酒数额。对此,笔者认为:(1)根据海关管理法规规定,自用红酒进口也应依法报关,但如有证据证实全部或部分货物(物品)确属自用,因自用不具备经营性质,该自用部分依法不应计入犯罪金额。(2)本案是否应扣除秦某、潘某的红酒金额,关键是陈某与二人是纯朋友帮忙还是销售关系,陈某有无从中获利。秦某、潘某二人称系从陈某处购买红酒,陈某称二人与其签订的也是销售合同。但由于大家共享叶某的进口渠道,如果陈某只是提供了收获地址的便利,并无从中牟利,则可据此认定秦某、潘某系部分进口红酒的实际货主,通过依法扣除秦某、潘某所购红酒金额,达到降低陈某走私犯罪金额的目的。
因此,本案应调查核实陈某自用红酒的数量,以及陈某与秦某、潘某之间是名义还是真实的销售关系,这是事实证据问题。对此,刑辩律师应在介入案件之初,就通过会见、阅卷、调查了解情况等一切可能的方式,努力发现侦控方的证据漏洞,并积极主动调取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构建本方证据体系。
四、本案辩护要点及风险点提示
陈某所在的XE商贸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红酒贸易,其应当熟悉进口红酒报关税率、手续,故走私犯罪故意很难否定。但单位走私的起刑点是偷逃税款20万元,本案如能认定为公司犯罪,即使犯罪数额32.8万元不变,根据本案犯罪情节、罪后表现,也很可能会对陈某改判定罪免刑。此外,如能查清并扣除陈某自用红酒数量,以及秦某、潘某所购红酒数量,本案犯罪数额可能大幅降低,甚至低于入罪标准。
需要特别提示的是,跨境电商模式作为国家为鼓励消费、便利跨境贸易推出的政策,有其明确的合规边界。该模式仅适用于个人自用、单次限量及年度限额内的商品进口,并享受相应税收优惠。进出口从业者务必严格区分一般贸易与跨境电商业务,不得将应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货物伪报、拆单伪装成跨境电商订单入境,否则不仅可能构成走私犯罪,还将面临刑事处罚和信用惩戒。一般消费者亦应注意,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购买商品时应如实申报、合理自用,切勿为贪图便宜或规避税费,与不法商家合谋以“化整为零”“代购分销”等方式违规进口,该类行为同样可能卷入走私链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梁雅丽,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主任,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执业近三十年,成功承办过多起重大有影响的刑事案件及民商事疑难复杂案件,并被国内多家媒体报道。她尤为擅长刑事和民商事交叉领域及刑事和行政交叉领域业务,致力于研究企业风险的法律防控,并先后为多家大型企业、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及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了出色的法律顾问服务。在企业风险的法律预防和控制、企业改制、资产重组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执业实践经验。《方圆律政》2014律政年度刑辩律师;《中国企业报》2017助力金融风险防范人物;《中国商报》2019年“商事法治建设年度典范人物”;《中国商报》2020年商事法治建设特别贡献奖;2021年度LEGALBAND中国律师特别推荐榜刑事合规15强,2022钱伯斯大中华区争议解决领域领先律师;2022品牌影响力·践行社会责任典范律师,2022年度LEGALBAND中国律师特别推荐榜商业犯罪与刑事合规15强;2023-2024钱伯斯大中华区争议解决领域领先律师;2024LegalOne客户信赖律师:商业犯罪与刑事合规15强;2024LegalOne客户信赖律师:杰出女律师(华北)15强;2024律新社年度标杆案例-商事犯罪领域;2024律新社年度律界女性领导力人物30佳;2025年GRCD-中国年度女律师;2025 ALB China十五佳诉讼律师。

傅庆涛,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系青岛科技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哈尔滨工程大学法律硕士实践指导教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员,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专业委员,《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曾在某沿海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近20年,从事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审判、财产执行及综合协调工作,原高级法官、首批员额法官,曾任刑二庭审判长、刑事综合组长。在《当代法学》、《人民法院报》等报刊公开发表/获奖调研文章数十篇,组织策划或参撰刑事审判工具书《刑法适用常见问题释疑》、《刑事案件常见罪名认定证据规范》,办理的合同诈骗罪案例被最高人民法院收录为《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性案例,内幕交易犯罪案例获全省二等奖。入职京都所以来,主要从事刑民执交叉案件研究和财产辩护/执行代理,专注于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大要案辩护,并在金融税务、文化娱乐、家族财富传承等领域进行耕耘,办理了大量经济犯罪、职务犯罪、涉财执行等案件,多起案件被公诉机关不起诉。在《法治周末》、《北京律师》等报刊及新媒体发表文章十余篇,参撰刑事辩护教科书《刑事辩护教程》(田文昌主编,202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合著《刑事涉财执行实务精要》一书(2024年法律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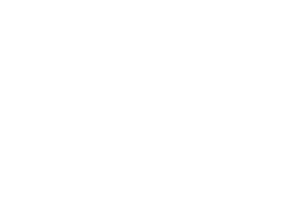
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