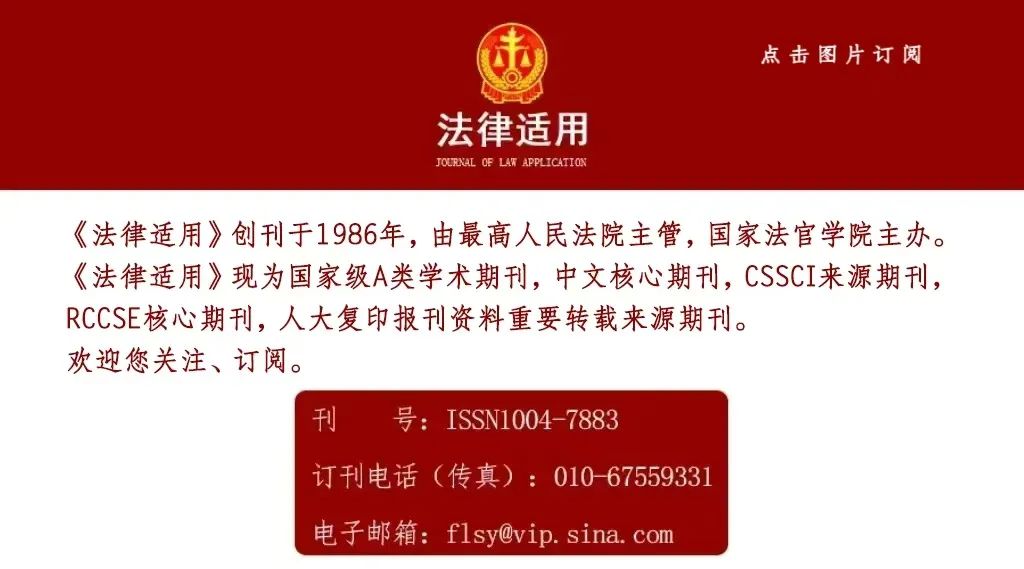来源:法律适用
发布日期:2025年09月12日
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律适用》微信公众号在推送纸质期刊文章外,特开设“实践法学笔谈”栏目,为务实管用的实践法学研究成果提供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 ,敬请关注!
编辑提示
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我国民法典的重大创新和亮点,人格权编的理解与适用是司法实践中的重点问题。伴随数字网络的广泛应用,一些利用互联网侵害人格权的新型纠纷开始出现,人民法院如何在新场景下准确理解民法典人格权编中的相关实体与程序规则,需要进一步的深入讨论。为此,本刊特邀 一线审判人员 ,围绕人格权纠纷审判实践中的疑难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以飨读者。


刘小梅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二级法官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拥有的网上精神家园,每个人都希望它清朗、和谐、健康。然而,网络空间时常被一些乱象所困扰,污染网络生态。2025年5月20日开始施行的《民营经济促进法》第59条第2款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互联网等传播渠道,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恶意侵害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人格权益。人格权益受到恶意侵害遭受实际损失的,侵权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文以一则通过互联网对首发新品发布不当言论的新型典型案例切入,围绕舆论监督合理边界的分析论证,探讨互联网名誉侵权行为的司法认定规则和考量因素。
一、基本案情
某文化传播公司系“YC家”品牌服装的经营者,首次获得“HF大学”相关作品及形象的创意元素设计、生产、销售的授权,并在抖音、快手平台发布关于其与HF大学联名的宣传广告,获赞10余万。姜某在某网络平台发布视频,就“YC家”品牌与HF大学联名一事发表不当言论,该视频浏览量为4万多次,某文化传播公司委托律师向姜某发送律师函要求其删除视频,姜某收到律师函后仅对视频中的服装品牌作了简单处理后再次上架。之后某文化传播公司经营的“YC家”淘宝网店服装销售量出现下降趋势。某文化传播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姜某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姜某抗辩认为某文化传播公司未取得HF大学的授权,发布的宣传广告属虚假广告,其发布视频是进行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的行为,且在之后采取了下架原视频、上架新视频的措施,故其并未侵犯某文化传播公司的名誉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姜某在未调查某文化传播公司发布广告真实性的情况下,擅自在其拥有众多粉丝的网络平台账户上发表含有侮辱、诋毁某文化传播公司的言辞,侵害了某公司的名誉权,致使该公司网店销售量下降。综合考虑 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影响范围及损害后果等因素,判决姜某在某网络平台本人账号上以视频方式发表道歉声明,赔偿某文化传播公司损失2万元、公证费1000元。
本案反映的问题是,应如何划定网络监督与侵犯名誉权的边界。网络舆论监督是信息化时代赋予公民的强大社会监督形式,然而其作用的有效发挥依赖于健康、理性、法治化的网络生态环境。伴随着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言论表达渠道的增多,网络论坛、微博、微信、视频网站等新媒体形式的出现已逐渐成为聚合民众意见、呈现公众情绪和各种思想观点碰撞的主要平台,网络舆论监督的主力军已经从传统的新闻媒体机构,转变为公民个人,这使得公众可以更为便捷地发表观点。但是,并非所有观点表达都可纳入为公共利益作出的“舆论监督”范畴,有时公众的网络评论并不是出于公共利益,而是可能夹带“私意”,借批评他人或假借舆论监督达到牟取私利之目的。[1]此时,行为人可能侵犯他人的人格权益。但如何把握正当的舆论监督行为与侵犯他人名誉行为之间的界限,存在一定的难度。
二、舆论监督的合理边界和侵权认定
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系“为公共利益实施的舆论监督”,关键在于从社会公共利益角度出发,判断行为人与权利人之间是否存在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否紧密、必要、合理。《民法典》第1025条规定了舆论监督行为的正当性阻却了行为人行为的违法性,因此行为人无需为侵害名誉权承担民事责任。而对于行为人是否具有不正当性即其是否构成侵权,一般需要从双方当事人的言论及其背景、是否超出必要限度、言论所针对的对象、因果关系以及损害后果等几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民法典》第1025条所列举的三种违法情形是对言论自由正当性的违背,事实的失真程度达到要受法律谴责的程度,使评论对名誉的侵害突破了公正合理的法律边界。有的行为人常常以其系为公共利益为由行使舆论监督权,故不构成民事侵权。但公共利益目的抗辩适用的前提之一是行为已然带来损害后果,并且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前提之二是行为人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公共利益目的抗辩之所以能够成为名誉侵权的特殊抗辩要件,根本原因就在于“为公共利益目的”阻却了“过错”要件的成立,这也是为什么《民法典》第1025条即使规定了公共利益目的抗辩,也仍然不保护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行为。[2]因此,民法典确定的公共利益目的抗辩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侵权的归责原则,而只是说,在存在公共利益的领域时,过错认定有利于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一方。[3]
具体到本案,某文化传播公司在取得与“HF大学”相关作品及形象相关的创意元素的IP品牌授权后,随即发布该首发新品的宣传广告,而作为在某网络平台拥有众多粉丝的UP主姜某,未对上述宣传广告作任何调查核实,即制作捏造、歪曲事实的小视频发布在其个人账户,甚至在视频中使用了侮辱性言辞诋毁某文化传播公司商誉。尽管其抗辩称此举系行使舆论监督权利,但纵观全案其并无“为公共利益”之动机,反而在收到某文化传播公司委托律师发送的律师函后,仅对服装品牌作简单处理后重新上架,可见其具有主观恶意,系对言论自由正当性的违背,加之某文化传播公司首发新品的消费群体与姜某粉丝群体的年龄段具有高度重合性,客观上造成某公司产品销量下降。如前所述,即便姜某发布视频是为了粉丝群体的利益,但其未调查核实某文化传播公司广告的真实性以及使用侮辱性语言贬损某文化传播公司商誉的行为均不具备公共利益目的抗辩的条件,属于《民法典》第1025条规定的三种免责例外情形,构成了对某文化传播公司名誉权的侵犯。
三、动态系统理论在人格权侵权责任中的运用
作为我国民法典的创新和亮点,人格权编中的多个条款正式明确采纳了动态系统论的立法指导思想, [4] 《民法典》第998条即运用动态系统理论,综合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后果等因素”。该理论最早由维尔伯格在比较法的基础上提出, [5] 动态系统论旨在明确法官裁判时应当考量各种不同的因素,以此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并改进以往立法中“全有全无式”的责任认定模式,目的在于协调和平衡人格权和其他利益之间的冲突。
在考量影响人格权侵权责任的各项因素时,其中关于双方当事人的职业对人格权侵权损害赔偿的认定非常重要,比如“周某驰诉中某无锡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肖像权、姓名权纠纷案”[6]中,侵权公司擅自使用周某驰的姓名、肖像用于商业广告,法院根据周某驰的职业身份、知名度、肖像许可使用情况以及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持续时间、主观过错程度、涉案侵权广告范围、网站公开程度、杂志发行量及可能造成的影响等,酌情认定财产性损失为50万元。[7]具体到本案中,法院在认定侵权损害赔偿时亦综合考虑了双方的职业,尤其是姜某的大学生身份以及姜某两次上架侵权视频的主观过错、侵权行为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其行为对公司造成的客观损害后果等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不同作用、不同程度等,酌情认定较为公正合理的损失金额。人民法院在对此类网络舆论监督行为加以规范和匡正的同时,也应注意发挥司法裁判的价值导向作用,通过对各种因素的互动综合考量,确定责任形式和赔偿范围等。
四、结语
随着自媒体时代到来,常有一些人员为了博取流量,以不当言论诋毁抹黑他人,致使合法经营企业商誉受损、首发新品销量下降。本案裁判提示,互联网言论自由亦有边界,靠侮辱、诽谤他人获取流量的行为不可取。法院积极延伸审判职能,针对该案向某网络平台公司发出“关于加强某网站用户文明上网监督力度”的司法建议,得到了该公司积极回复,表示网络平台将大力开展不文明内容的治理工作,并针对侵权申诉场景进行分级处理,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注
释
[1]参见彭桂兵、丁奕雯:《论〈民法典〉中“新闻报道”与“舆论监督”之意涵》,载《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1期,第160页。
[2]参见王雨亭、秦前红:《名誉侵权中的公共利益目的抗辩——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特殊免责事由》,载《河北法学》2022年第2期,第180页。
[3]参见刘文杰:《〈民法典〉在新闻侵权抗辩事由上的探索与创新》,载《新闻记者》2020 年第 9期,第 65 页。
[4]参见王利明:《〈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立法亮点、特色与适用》,载《法律适用》2020年第17期,第5页。
[5]参见[日]山本敬三:《民法中的动态系统论——有关法评价及方法的绪论性考察》,解亘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3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
[6]周星驰诉中建荣真无锡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肖像权、姓名权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0年第2期,第43-48页 。
[7]参见刘力、何健:《人格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司法运用与完善——以“周星驰肖像权、姓名权”纠纷案为例》,载《法律适用》2020年第4期,第71页。
文字编辑:王常阳
排版:孙鹏庆
策划:姜 丹
执行编辑:刘凌梅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仅供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参考。

扫上方二维码订阅
点击名片关注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