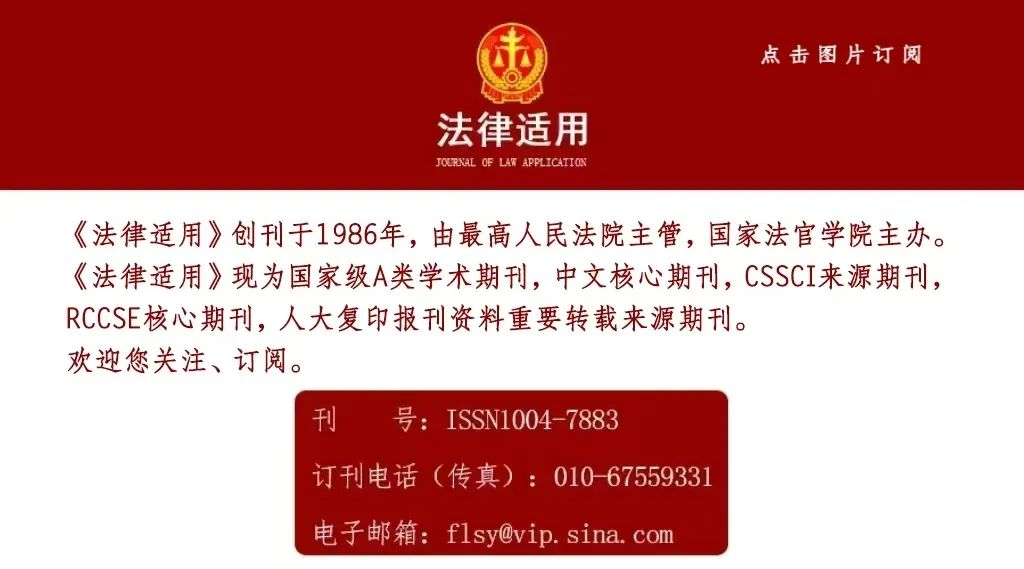来源:法律适用
发布日期:2025年09月12日
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律适用》微信公众号在推送纸质期刊文章外,特开设“实践法学笔谈”栏目,为务实管用的实践法学研究成果提供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 ,敬请关注!
编辑提示
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我国民法典的重大创新和亮点,人格权编的理解与适用是司法实践中的重点问题。伴随数字网络的广泛应用,一些利用互联网侵害人格权的新型纠纷开始出现,人民法院如何在新场景下准确理解民法典人格权编中的相关实体与程序规则,需要进一步的深入讨论。为此,本刊特邀一线审判人员,围绕人格权纠纷审判实践中的疑难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以飨读者。


季佳彬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周浦法庭二级法官助理
舆论监督作为宪法言论自由权利的延伸,是社会监督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肖像权作为人格权的重要类型之一,也是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在特定情况下,二者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法律冲突,因此明确舆论监督中肖像权的合理使用标准,对平衡言论自由与人格权保护尤为重要。我国《民法典》第999条规定,为公共利益实施舆论监督等行为的,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体的肖像。《民法典》第1020条第1款第5项规定,为维护公共利益等,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的,属于肖像权的合理使用,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1]法答网第19批精选答问(人格权专题)问题2针对在舆论监督中肖像权的合理使用认定进行了分析解答,为此类案件审理提供了指引参考。本文以该答问为视角,结合实践中相关典型案例,就舆论监督中肖像权合理使用的认定进行探讨。
一、案情介绍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肖像权网络侵权案件,原告孙某系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男明星,某网络公司在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标题涉及孙某的姓名及含有“被网友痛骂……”等字眼的文章,并在文章中配有原告的肖像图片5张,阅读量为8698次,且在文章末尾位置植入了官方微信二维码等信息。孙某主张该网络公司未经自己同意,擅自使用包含自己肖像的图片进行商业引流、推广服务等营利行为,具有明显的商业使用属性,侵害了原告的肖像权。某网络公司认为所发文章系行使舆论监督权,有权使用孙某的照片,且没有对被告的肖像进行任何丑化、贬损,原告作为公众人物,对肖像被使用应当有更高的容忍义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某网络公司发布的文章标题和内容,其使用孙某照片的行为目的在于吸引读者,进行引流,显然不属于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的范畴,其擅自使用孙某照片的行为构成肖像权侵权。
二、正当舆论监督的司法认定标准
舆论监督目前并无严谨的法律定义,司法实践中亦不做明确的规定,而是直接认定某种表达是否属于舆论监督的范畴。[2]但根据学理通说,舆论监督是指社会公众依法通过媒体发表评论,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进行评论,实行监督。[3]笔者认为,正当舆论监督司法认定的标准应包含两个方面:舆论监督对象的认定和舆论监督行为的认定。
(一)舆论监督对象的认定
通常而言,舆论监督的对象为公众人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体育影视明星等),即上述对象因掌握国家权力或者对公共利益造成较大影响,涉及到社会大众的普遍利益,因此成为默认被监督的对象。在特定情况下,一般公众因某些重大事件或涉及公众利益等亦有可能成为舆论监督的对象。值得讨论的是,在民事主体的名誉权保护中,学界和实务界通常会对公众人物和一般公众进行区分,在肖像权保护中,该种区分是否亦可延续适用值得更深一步探讨。
公众人物和一般公众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具有较广的人际关系、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和关注度,因此在其享受公共资源的同时,当然应当成为公众知情权和公民批评监督所直接指向的对象,[4]基于监督的需要,相较于一般公众,可以对其肖像权等人格权进行必要限制。在司法实践中,肖像权侵权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营利为目的擅自使用;二是对他人的肖像毁损、玷污;三是一般使用行为。在对公众人物肖像权限制上,应当侧重于第三项。在舆论监督中,对公众人物的肖像存在一般使用行为的,如用公众人物照片作账号头像,或者在相关主题贴文中使用公众人物照片的,未实施侮辱、恶意损害行为的,通常不应认定为侵权。
(二)舆论监督行为的认定
要求使用人使用肖像权的行为客观上应有利于公共利益,即能够披露不法或不正当行为,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至于使用者在使用时主观动机则在所非问,即便使用者并非为公共利益的动机进行舆论监督,在其行为客观上有利于公共利益时,也应当认定构成为公共利益,不成立侵权。
实践中存在争议的是,当行为人的使用行为为公益也兼为私利,即使用的结果不仅有利于公共利益,同时也为使用人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如借舆论监督进行网络引流、推销服务、推广商品等商业宣传时,是否构成对肖像权的合法有效使用。笔者认定,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进行判断,或认为只要存在谋私利的行为均为侵权,实践中不宜为舆论监督设置较高的门槛。原因在于,通常而言,进行舆论监督通常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甚至需面对各种压力甚至可能的不利影响,从鼓励和保护舆论监督的角度,应采动态系统论的方式,即对舆论监督主体身份,舆论监督标题和内容、舆论监督主体的历史发布内容、舆论监督的时间、被监督对象的身份等进行综合认定,如构成显属(主要为)营利性使用的,可以认定为属于侵害他人肖像权,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三、舆论监督中肖像权合理使用的认定规则
舆论监督的正当性是认定肖像权合理使用的前提,也可以说非正当的“舆论监督”超出了监督的应有之义,系以监督之名行侵权之实,实际已非本文所称的舆论监督,故不存在合理使用的可能。同时,(正当的)舆论监督中适用肖像权亦须遵循一定的要求,通常而言,认定舆论监督中肖像权使用系属合理需同时满足以下两点:使用行为存在必要性和使用行为本身的适当性。
(一)使用行为存在必要性
使用行为应存在必要性,即使用他人肖像是不可避免的、必须的,若不使用无法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在张某诉某文化传媒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5]中,法院认定实施舆论监督可以未经肖像权人许可,必须满足使用是不可避免的,必须的。对于必要性的判断,一是行使手段上,使用行为是舆论监督的必要手段,他人的肖像对于舆论监督的目的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不可或缺性。如使得舆论监督行为成立有效,使监督对象得以确定明晰,避免偏差和模糊。二是最终结果上,使用行为具有增益性,通过使用他人肖像,能够有助于舆论监督的传播,有助于提升舆论监督的效果,有助于提升舆论监督精准度,在客观结果上有助于舆论监督目的的实现。
舆论监督中的肖像权使用不同于新闻报道,应当区分二者在认定肖像权合理使用时的不同。因新闻报道含有为公共利益的内在意思,要求具备真实性和完整性,且需满足一定的资质,[6]因此《民法典》第1020条第2项规定,只要求“不可避免”,并未要求为公共利益。舆论监督则无新闻报道的诸多前置条件,因此需要以“公共利益”对其进行概括限制,防止不正当舆论监督中对肖像权的滥用。
(二)使用行为本身的适当性
在舆论监督中使用他人肖像,使用行为本身应当合理、适当,不违背公序良俗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如为公共利益实施舆论监督等行为所制作、使用、公开的肖像应当具有合法来源,不得以非法侵入、侵害他人隐私、不正当偷拍偷摄等获取他人肖像。同时,使用手段应当具备一定的相当性,使用手段与舆论监督目的之间符合比例原则,即使用他人的肖像权能够服务于舆论监督目的,能够增强舆论监督行为的说服力,有助于提升舆论监督的传播力。此外,在使用当事人的肖像时应采取必要、合理的保护措施。比如,在舆论监督不可避免使用未成年人肖像时,就有必要通过打马赛克等方式对未成年人权益进行进一步保护。即对肖像权的制作、公开、使用,是为公共利益实施舆论监督等行为所必须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施某某、张某某、桂某某诉徐某某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纠纷案”的裁判要旨即认为,为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和揭露可能存在的犯罪行为,发帖人在其微博中发表未成年人受伤害信息,使用了施某某受伤的九张照片(使用时已经对脸部作了模糊处理),所发微博的内容与客观事实基本一致,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不应认定此行为构成侵权。[7]此外,对合理使用的认定,还需要结合《民法典》第998条的规定,结合动态系统论的方法,综合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后果等因素。
四、舆论监督时肖像权侵权的牵连性认定
为公共利益实施舆论监督时,特定情况下存在和名誉权等人格权相互牵连的情形。如为公共利益,以发表批评、评论文章等方式进行舆论监督时,其内容虽然为真实,但用词存在贬损性,侮辱性,可能构成名誉权侵权,同时使用其肖像的,是否亦构成肖像权侵权也存在争议。若将名誉权与肖像权简单剥离来看,似乎不构成侵犯肖像权,因为未直接对肖像本身进行涂改、毁损、玷污,但从整体来看,侮辱、贬损的对象正是文章的肖像权利人,构成对肖像的侮辱性使用,应当成立对肖像权的侵权。由此,在与其他人格权形成牵连的情况下,应当综合舆论监督整体内容、舆论监督的目的、牵连的深度、肖像的内容等因素进行综合认定。
五、结语
肖像权作为自然人的外部形象,能够直接反映特定自然人的外部形象特征,与人格尊严紧密相关,同时兼具经济价值,因此系一项重要的人格权。而舆论监督代表的言论自由,系民事主体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途径,且舆论监督的样态丰富,内容复杂。因此在二者存在冲突时,首先应当认定该舆论监督是否正当,在此基础上,以使用行为是否必要和使用行为本身是否适当两个角度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在当今社会,“人的肖像”已经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重要构成部分,[8]与此同时,全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主体、内容和载体也发生了深刻演变,通过为舆论监督中肖像权的使用划定合理边界,实现舆论监督的有序开展,进而维护清朗的肖像社会空间秩序,不断筑牢数字时代人格权保护的防线。
注
释
[1]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民法典》第1025条的规定,其将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置于同等地位,鉴于新闻报道可能涉及新闻监督,也可能涉及单纯信息传播,结合新闻报道采编和发布主体的特殊性,对肖像权的使用有其特定规范要求,故本文仅探讨狭义舆论监督中肖像权的合理使用规则。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第1版,第278页。
[3]参见王强华、魏永征:《舆论监督与新闻纠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4]参见沈志先主编:《侵权案件审判精要》,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页。
[5]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04民终22号。
[6]参见彭贵兵、丁弈雯:《论〈民法典〉中“新闻报道”与“舆论监督”之意涵》,载《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1期,第159页。
[7]最高人民法院 (2015)江宁少民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
[8]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页。
文字编辑:王雪川
排版:孙鹏庆
策划:姜 丹
执行编辑:刘凌梅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仅供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参考。

扫上方二维码订阅
点击名片关注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