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发现律师事务所
发布日期:2025年11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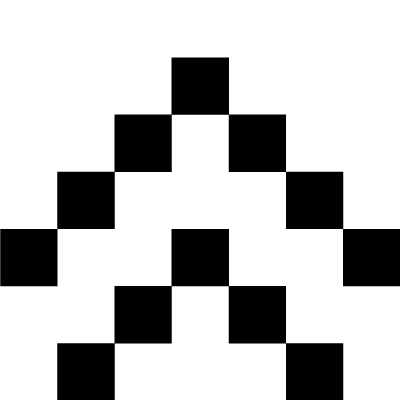
关注 发现 ,认识更多有温度、有灵魂的法律人


作者: 左梓钰
关于“戏仿作品的著作权法规制”问题之详细研究,请参阅左梓钰博士发表在SSCI期刊《玛丽女王知识产权杂志》(Queen Mary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2023年第2期上的On the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Parody in the New Copyright Law of China(论戏仿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的解释)以及发表在CSSCI期刊《知识产权》杂志2020年第7期的《论合作作品的著作权法规范》
引 言
我国著作权司法实践关于戏仿问题的讨论很少,即使正面遇上,最终通常“擦肩而过”,这不失为我国著作权法实践的遗憾。而一个本可以成为类似美国版权司法实践中经典判例的“《漂亮女人》”案之“《五环之歌》案”,却没能成为我国著作权司法实践史上涉戏仿创作之经典案例,更是遗憾中的遗憾!在“《五环之歌》案”中,原告众得公司经词作者乔羽的授权依法独占享有《牡丹之歌》的词作品及其音乐作品著作权之共有权利的著作财产权。而以知名相声演员小岳岳(岳龙刚)等为代表的被告未经众得公司许可,将《牡丹之歌》改成了一首集戏曲和摇滚为一体的《五环之歌》并将之进行商用,于是被诉至法院。[1]该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改编且不能构成著作权的例外,从而侵害原告之著作财产权?本文认为《五环之歌》可以成立戏仿作品并对戏仿的著作权法规制进行分析。同时,本文在此呼吁我国法实践人员在相关问题上可以再进一步,法治进程需要法学研究与实践的携手共进。
一、 什么是戏仿
戏仿(Parody),又称滑稽讽刺或滑稽模仿。流行的戏仿定义是指以讽刺或批评为目的,“对一部作品形式上的模仿、内容上的改变”。[2]广义的戏仿还包括后现代主义环境下产生的拼凑,即通过拼接重组不同作品部分的内容以表达新的意义,这种作品被称为“挪用作品”。戏仿一词虽是舶来品,但这种创作在我国源远流长,只是当时并未称之为戏仿。所谓戏仿的文作被划分在了“重述”(或“重写”[3])的文作之中,该重述是指“重释性叙述”。[4] 比如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补》就是《西游记》的戏仿之作,又比如我国现代时期鲁迅的《故事新编》、郁达夫的《采石矶》、郭沫若的《漆园吏游梁》和《柱下史入关》、废名的《石勒的杀人》、冯至的《仲尼之将丧》、王独清的《子畏于匡》、欧小牧的《七夕》等等。至我国当代,典型的戏仿有大话(无厘头)、恶搞创作等,如经典喜剧《大话西游》、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总之,戏仿是“一种结合了多种不同表达方式的、讽刺性或批评性的模仿,这种表达因内在不同表达方式间的矛盾和差异而产生出滑稽的效果。”[5]就《五环之歌》而言,其对《牡丹之歌》所引和所修的部分,依据戏仿之概念,应当构成戏仿创作。而且法院对《五环之歌》主旨作总结时,也指出该歌所引部分具有“戏谑性”,或说“讽刺性/批判性”。
二、 戏仿在我国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问题
我国涉戏仿的著作权诉讼基本由具有“中国迪士尼”之称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提起。在一起直接涉及戏仿问题的“网络文章使用动漫形象案”中,原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享有动画片《葫芦兄弟》中“葫芦娃”这一美术作品的除署名权以外的著作权)认为被告微世界传媒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的《在魔都娶个老婆等于娶了7个葫芦娃》文章未经许可,使用了7幅“葫芦娃”美术作品,故将被告诉至法院。但被告辩称其文章对涉案图片的使用是为了说明上海女性在各种生活场景下的表现,并非为了展现涉案图片的艺术性,而是赋予了涉案图片新的意义,属于“戏仿性”创作,构成著作权例外规范中的“适当引用”。但法院在审理该案时,跳过了关于被告戏仿行为性质的分析,而是以被告没有“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即著作权例外规范的“指明来源”要件)为由直接认定被告行为构成侵权。[6]在另一起“网络喜剧使用动漫形象案”中,被告未经原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许可,在其网络情景喜剧《数码贱男》的第二季第八集中插入了13秒左右的关于《葫芦兄弟》中7个葫芦娃的视频,并主张其行为构成“适当引用”。法院虽认可被告的行为属于适当引用,但因为被告没有满足著作权法关于著作权例外规范的指明来源要件,且不存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13,下文简称《实施条例》)第19条规定的情形,[7]故认为被告行为不构成著作权的例外。[8]
但在与前述案例相反的另一起经典的“电影海报使用动漫形象案”中,两审法院通过分别借鉴美国版权法中的合理使用规则和“转换性使用”理论,均以“适当引用”肯定了电影海报使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享有著作权的八零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动漫形象“黑猫警长”和“葫芦娃”作为其宣传背景的行为,并认为未指明原作品名称和作者名是受海报创作及其使用方式的限制,不影响被告行为构成著作权的例外。[9]
可见戏仿在我国著作权司法实践中虽然一般被认定为适当引用,但法院对于戏仿是否符合著作权例外之另两步检验或两要件的看法并不一致。
三、 戏仿创作构成著作权的例外
虽然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关于著作权例外之规定)在特定情形中增加了一项兜底条款,但该条款有严格限定,即必须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换言之,无法律或行政法规之规定,法院不得自行创设例外情形,故我国著作权法的自由无偿使用制度仍是封闭模式。要符合著作权的例外,必须满足“三步检验法”:法定的特别情形、指明来源要件(“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和“两不得”要件(“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既然实践对于构成“适当引用”情形无争议,本文主要分析戏仿是否符合“指明来源”和“两不得”要件。依据学术诚信原则,使用他人作品时指明来源是天经地义,但是否所有使用别人作品的情形都方便指明来源,或者只要没有指明来源而使用作品的行为就不诚信,值得商榷。由此,《实施条例》第19条就规定了不指明来源的例外,条件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因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而无法指明”。戏仿创作就是一个“因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而无法指明”的典型。戏仿的对象通常是在社会中有一定热度的对象,因而人们一般不会对原作品的归属产生混淆。戏仿的创作习惯不要求戏仿作品必须指明来源,戏仿的滑稽讽刺或幽默批评需要人们自己去感悟,而不是让戏仿者把作品与作品之间的链接一五一十地给人们呈现出来,否则便失去了戏仿的意义。因此,法院对于著作权例外规范中指明来源要件的解释,必须结合不同作品的创作习惯和不同行业领域的引用惯例来进行分析,不能对指明来源要件和《实施条例》第19条作机械地解读。
通常情况下,戏仿作品构成对原作品的实质性使用。戏仿是对原作品的戏谑性模仿,为了突出对比从而达到良好的讽刺或批评效果,有的戏仿作品甚至要从一定程度上突出其所指,可能出现长篇引用的情形。但戏仿作品不会构成对原作品的实质性替代。戏仿是在模仿原作的基础上又加入戏谑、搞怪、夸张等成分,从而形成一种与原作内容和风格都截然不同的新作品,构成“转换性使用”。戏仿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通过现作品联系到原作品从而产生“互文性”的讽刺或批判的效果。换言之,戏仿不会导致公众对创作来源的混淆,不会触及原作品的市场,不会对著作权人的市场收益有所减损,因而不会影响著作权人对原作品的正常使用。在是否会“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问题上,既然不会影响原作品的市场,自然不会损害著作权人的著作财产权。可因为戏仿涉及对原作品的滑稽讽刺,因而有侵害著作人格权(主要涉及保护作品完整权)之风险。如何理解保护作品完整权中“歪曲、篡改”之意,本文认为,对于已发表的作品而言,应当采“歪曲、篡改”认定的客观标准(“读者意思”标准)。戏仿是“一种出于个人利益考量而无意中创造的公共善品”,[10]通过讽刺或批评的方式是戏仿创作的基本规律。戏仿是创作的基本形式之一,所以保护作品完整权必须对这种创作予以包容。著作权法宗旨是鼓励创造,创造是建立在知识的传播之基础上,而保护作者的著作权及其相关权是服务于整部法目的的手段。因此,对作者权益的保护不能挟持社会创新,保护作品完整权不能成为作者抑制后人创作的万能钥匙。
注释:
[1] 参见天漳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6民初1980号和天津第三中级人级法院(2019)津03知民终6号民事判决书。
[2] 玛格丽特·A.罗斯:《戏仿:古代、现代与后现代》,王海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至44页。
[3] 参见刘桂茹:《先锋与暧昧:中国当代“戏仿”文化的美学阐释》,江苏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9至10页。
[4] 参见董上德:《古代戏曲小说叙事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至154页。
[5] 左梓钰:《论将戏仿纳入著作权法合理使用制度的正当性》,中国政法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7页。
[6]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5民初18896号民事判决书。
[7]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13)第十九条:“使用他人作品的,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由于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无法指明的除外。”
[8]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知民初字第1114号民事判决书。
[9] 上海普陀区人民法院(2014)普三(知)初字258号民事判决书和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5)沪知民终字第730号民事判决书。
[10] 苏力:《戏仿的法律保护和限制———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切入》,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第7至16页。
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