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刑事法库
发布日期:2025年11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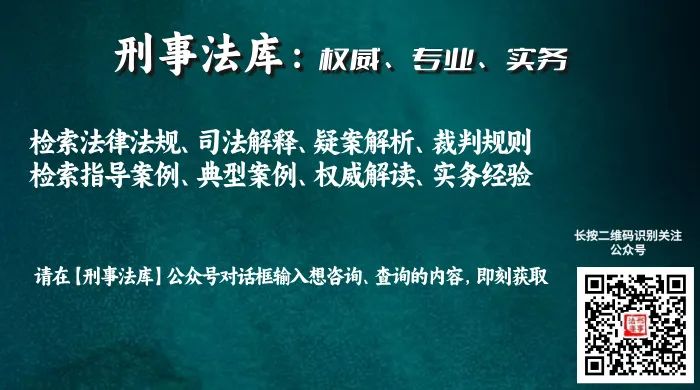
摘 要: 在建筑工程领域,层层转包现象普遍存在,由此引发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适格主体认定问题,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争议不断。此类争议的核心在于如何准确界定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边界,避免将行政法上 的连带清偿责任直接等同于刑法上的作为义务。实际施工人作为劳动关系的直接相对方,应当认定为该罪的适格主体;中间转包方虽在行政法上负有清偿责任,但因缺乏直接的劳动关系基础,不应成为刑事责任主体。刑事责任的认定必须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维护合同相对性,并充分体现刑法的谦抑性。
关键词: 犯罪主体认定 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界分 合同相对性 法益保护平衡
全文
一、基本案情
2022年11月9日,发包方A公司将其某项目营销中心的装修工程以总价包干方式发包给总承包方B公司,合同总价为144余万元。同日,B公司在未取得A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以112余万元的价格将该装修工程整体转包给C公司,双方签订《工程转包合同》,合同内容除工程价款降低外,其余关于工期、工程质量等条款基本沿用A公司与B公司签订的合同,且未对劳动者工资支付责任作出特殊约定。随后,C公司又以相同价款将工程转包给实际承包人赵某某,因赵某某不具备承接工程的相应资质,其挂靠在D公司名下,以D公司的名义与C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工程的施工组织、人员雇佣、资金管理等均由赵某某独立负责。
赵某某承接工程后,于2022年10月10日开始组织人员施工,先后雇佣24名工人参与施工。2022年12月15日,该装修工程如期完工,A公司于2022年12月20日按照合同约定向B公司支付了约122万元工程款。B公司收到工程款后,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未向C公司支付相应工程款;C公司因未收到B公司的付款,也未向赵某某支付工程款,最终导致赵某某无力支付24名工人的工资,共计拖欠工资712801元。
2023年12月5日,部分工人因长期无法拿到工资,向当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当地负责辖区内劳动保障监察及工程建设领域监管工作的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12月10日、2024年1月8日,先后向B公司、C公司、D公司发出《责令限期支付通知书》,要求三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核实并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但三公司均未在限期内履行支付义务。
2024年1月25日,在当地管理委员会的主持下,B公司、C公司以及赵某某就拖欠工人工资的支付问题进行协商,最终签订《工资支付协议》。协议约定:B公司于2024年2月10日前向工人支付43万元,C公司于2024年2月15日前向工人支付14万元,用于优先清偿部分工人工资;剩余142801元工资由B公司于2024年6月30日前支付完毕,赵某某对工资支付情况承担监督责任。协议签订后,B公司按照约定于2024年2月10日支付了43万元,但C公司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未按期支付14万元工资。2024年2月23日,当地公安机关接到当地管理委员会的案件移送后,对C公司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一案立案侦查。2024年2月28日,C公司在得知被立案侦查后,向工人足额支付了14万元工资。
二、分歧意见
本案涉及多方主体,法律关系层层嵌套,核心争议焦点在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适格主体认定,主要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C公司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该观点认为,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29条、第30条,中间转包方对农民工工资负有连带清偿责任。C公司未按协议支付工资,经行政机关责令后仍拒不履行,符合该罪构成要件。
第二种意见认为,C公司不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适格主体,不构成犯罪。该观点主张,刑事责任主体认定需遵循罪刑法定与合同相对性原则。赵某某作为实际雇主,是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定义务人,而C公司与工人无直接雇用关系,未支付工程款属于民事违约,而非刑事犯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即C公司不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适格主体。具体从以下维度展开分析:
(一)行政清偿责任与刑事作为义务存在功能与性质上的差异
在我国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法律规范体系中,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虽然在价值目标上均致力于实现公平正义,但在责任性质、价值取向及法律后果等方面存在显著区别,应当予以明确区分。
为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我国相继制定多项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明确建设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及分包单位对农民工工资支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外,还确立了政府在特定情形下的兜底清偿责任。
从责任的法律性质来讲,《条例》确定的中间转包方对农民工工资的连带清偿责任,属于行政法层面的责任,具有明显的行政调控性和政策指引性,其目的在于通过行政手段及时解决特定时期建筑工程领域农民工工资拖欠这一社会突出问题,体现了行政法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规定的是刑法层面的责任,具有强烈的惩罚性和威慑性,其设立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刑罚这一最后保障手段,惩治和预防恶意欠薪行为,以弥补民事与行政救济不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正常的社会秩序。
关于本罪适格主体的认定,本质上反映出刑法与行政法在价值立场方面存在的不同标准。主张C公司是本罪适格主体的观点,实质上是将《条例》确立的“清偿责任”直接等同于刑事犯罪中的“作为义务”,这一理解混淆了不同法律责任的界限,存在明显的法理上的瑕疵。《条例》第29条、第30条规定的连带清偿责任,是行政机关为保障弱势群体权益作出的一种风险分配和制度安排,目的在于扩大保障力度。而《刑法》第276条之一规定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中的作为义务必须源于行为人对法益侵害的实质性支配和控制能力。倘若不进行实质性审查,直接将行政责任提升为刑事作为义务,会模糊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之间的清晰界限,不仅对建筑行业主体之间正常的交易秩序构成威胁,也会破坏刑法的谦抑性。
另外,《条例》第30条明确规定承担了农民工清偿责任的建设单位或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等主体依法享有追偿权,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否定了刑事责任的可传导性,否则将出现“民事追偿权”与“刑事应罚性”的逻辑悖论。
为此,必须划清行政判断与刑事判断的界限,在定罪时基于犯罪构成进行实质性审查,避免直接将行政责任上升为刑事责任,进而保护刑法的谦抑性。
(二)违法转包不应成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
我国建筑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非常复杂,从本质上分析,根本原因是建筑领域发包承包的乱象。有观点认为,转包方违法将工程转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挂靠个人,客观上增大了工人工资无法支付的风险,因此应追究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刑事责任。该观点的核心逻辑在于将客观风险来源等同于刑事可罚性依据。然而,该主张混淆了行政法上的风险分配机制与刑法上的个人归责原理。刑事责任的认定须以行为人具有刑事非难可能性为基础,而非简单追溯风险来源。
首先,建筑工程领域的违法转包和挂靠行为,违反了《建筑法》第26条、第28条等规定,该行为所增大的风险属于行政法层面的风险分配与管控范畴,而非刑法意义上的具体、紧迫的法益侵害风险。行政法规层面的连带清偿责任本质是基于政策考量对市场风险进行强制性再分配,是一种以“效率优先”为价值取向的风险分配机制。而《刑法》中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其规制的是行为人对其已实际支配且可控的法益侵害风险的漠视与恶意回避。C公司作为转包方,其未支付工程款的行为确实可能导致下游资金链断裂,但这种风险属于其与赵某某合同关系中的履行风险。C公司对工人的工资支付并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实质支配力。以行政法创设的风险责任机制,直接推导刑事可罚性,实质上是将刑事责任判断建立在风险分配而非客观行为之上,这将导致刑事责任承担范围的无限扩大。
其次,刑事归责必须以行为人具备主观罪过为前提,而违法转包行为与欠薪结果之间缺乏刑法上的主观归责基础。刑法中的责任主义原则要求,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必须以其具备故意或过失为前提。对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而言,行为人必须对“不支付劳动报酬”这一核心行为具备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负有支付义务且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C公司作为转包方,客观上其“不支付”行为指向的对象是赵某某而非工人,主观上其明知的内容是赵某某本人不具备相应资质,对其“未支付”最终可能发生的欠薪后果,至多存在某种抽象的、间接的预见可能性,但这种预见可能性与刑法所要求的、对自身行为侵害劳动者财产权的具体故意截然不同。追究C公司的刑事责任,实质上是创立了一种“担保责任”,即为其下游主体的支付能力提供刑事担保,这完全背离了刑法责任主义所要求的个人罪过原则。
(三)合同相对性限定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责任主体范围
合同相对性原则是指合同仅对缔约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对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这一原则是民事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之一,贯穿于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以及违约责任追究等各个环节,对于维护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具有重要意义。在建筑工程此类涉及多重合同链、主体关系复杂的领域中,合同相对性对确定各方权利义务边界具有尤为关键的指引作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关系虽然牵涉建设单位、总包单位、分包单位及实际施工人等多方主体,但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仍应以合同约定为依据,严守相对性原则,避免责任关系的泛化和混乱。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犯罪主体应为直接负有支付劳动报酬义务的自然人和单位。这里的“义务”须源于合法的劳动或劳务关系,体现为用人单位或雇主对劳动者个人所负有的、具有人身专属性和对价性的工资给付责任。以本案为例,存在两组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一是C公司与赵某某之间的建设工程转包合同关系,属民事承包范畴;二是赵某某与其招用的工人之间形成的事实劳务关系。赵某某作为实际雇佣、管理并使用工人劳动的直接用工者,是劳务合同事实上的相对方,依法负有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定义务。C公司作为上游转包方,其合同义务的对象是赵某某而非工人,其义务内容为依转包合同支付工程价款,而非支付工人工资。C公司未按约支付工程款的行为,固然可能在事实上导致赵某某资金链断裂、无力支付工资,但这种违约属于前一民事合同关系中的责任问题,与后一劳务关系中的工资支付义务不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关联。C公司既非工人的用人单位,也与工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用工合意,因此不具备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所要求的“支付义务主体”资格。若仅因C公司未付工程款这一民事违约行为间接引发欠薪后果,就突破合同相对性追究其刑事责任,实则混淆了民事违约与刑事犯罪的界限,导致刑法过度介入民事领域,破坏法律体系的稳定性。
(四)劳动者报酬权与市场主体经营安全的平衡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规定在《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其核心法益是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即劳动者依法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劳动者通过提供劳动获取劳动报酬,是其维持基本生活、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保障,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民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刑法》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旨在通过严厉的刑事制裁,打击恶意拖欠劳动者劳动报酬的行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刑法在保护劳动者劳动报酬权的同时,应当兼顾市场主体的经营安全法益。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参与者,其经营安全和预期稳定性是法治经济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石。若将刑事打击范围过度扩展,将间接关联主体纳入犯罪主体范围,将不当加重企业运营风险,抑制市场活力。在建筑工程领域,中间转包方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其参与工程转包业务是正常的经营行为,其支付能力往往受制于上游工程款结算、工程质量验收、合同履行争议等多重因素。若将其认定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适格主体,会使中间转包方面临巨大的刑事风险,影响其正常的经营活动,进而影响市场秩序的稳定。
司法实践中,在处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时,应当在劳动者权益保护与市场主体经营安全之间寻求平衡。具体而言,应当明确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适用边界,仅将与劳动者存在直接劳动关系、负有直接支付劳动报酬义务,且故意拖欠劳动报酬的主体认定为该罪的适格主体。对于中间转包方等与劳动者无直接劳动关系的主体,即使其负有行政法上的连带清偿责任,也不应将其认定为该罪的主体,以保护其经营安全和正常市场秩序。如果直接将C公司认定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主体,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使劳动者拿到工资,但损害了C公司的经营安全,违背了法益保护的平衡原则,也不利于建筑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四、结语
在建筑工程领域层层转包的情形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适格主体的认定,应当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合同相对性原则,明确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界限,平衡劳动者权益保护与市场主体经营安全。虽然行政法规定中间转包方负有支付农民工工资连带清偿责任,但该规定仅是行政法规的政策性规定,不能突破上位法的基本原则。与劳动者之间不存在直接劳动关系的市场主体,不属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适格主体。实际施工人作为与劳动者存在直接劳动关系的主体,负有直接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若其实施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应当认定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适格主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案折射出劳动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深层矛盾:行政监管与刑事制裁的衔接问题;特殊行业政策与普遍法律原则的冲突问题;弱势群体保护与市场主体经营安全的平衡问题。建议通过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建立阶梯式的责任追究体系:首先,利用行政手段促使相关市场主体履行其清偿责任;对拒不配合者,可考虑采取行政处罚措施;对与劳动者存在直接劳动关系的市场主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加强工程款支付监管、完善民事追偿途径以及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等措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农民工工资权益保障体系。这种处理方案既坚守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底线,保持了法律体系的内在协调,又兼顾了我国现阶段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实践需要,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来源: “中国检察官”微信公众号,2025年11月15日。作者: 王兴周,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李孟飞,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五级检察官助理。






